作者:冯湘湘
武侠浪漫化和「优雅的暴力」
把武侠和武功招式浪漫化,是柴田炼三郎最吸引人的风格。他写武打不喜欢一拳一脚、刀来剑往的真功夫,而是喜欢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尤其擅于描写气氛环境,并以此来衬托场面的险恶和突出人物心理活动,文字凄美激情,形成一种「风雅的艺术」之另类武侠小说特色,亦即评论家所谓的「优雅的暴力」,这留给读者深刻印象。请看如下描写:
「到处留有雪迹的院内听不到鸟啼声,也无风声,寂静得怕人。只冬阳把两人的影子无声无息地移动着。
胜负就在剎那间结束。」
「那是月光照不到地面的密林。
水鸟飞起正表示该处充满敌人迎击的杀气。
己到了每一步都是死地了,任何一棵树木背后,都可能有敌人匿藏。
杀气充满整座林子。
呃,来了。
就像仰慕杀气,一阵强烈的风刷地掠过树间,当他摇响树叶,飞上高空,再度恢复静寂时,左右暗处响起尖锐的弦音。
下一剎那,二枝箭已断成两截。」
「源四郎快似魔影,奔了三间余。
边跑边拔出短刀投向前方的暗处。
看似樵夫堆积的背后响起惨叫。
他发挥着掠鸟的速度,边以长剑水平地画道弧圆。
弧线的中央是一棵树,树干蓦地折断。
树身缓缓倒下,令埋伏高枝上的伏兵十分狼狈。
人树倒地,发出巨响时,源四郎已离开树林,站在池畔的草丛中。
忽地,两边灌木斜里剌出多把矛枪。
七、八个黑衣的敌影一齐从草丛里站起来……」
有情有景、有声有色。虽非复杂的拳脚功夫大比拼,但看惯古龙作品的人定会明白,柴田这种简单却充满动感和电影感;并以环境气氛衬托激战的浪漫手法,正是古龙最擅长的表现技巧。
古龙曾说过:「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他有感于武侠小说中,武打设计的硬桥硬马和繁复无趣,因而将武打设计为简洁明快、一招见效,并注重武打气氛的营造,相信应曾受柴田作品的启发。
武侠之至高境界——「剑禅合一」
日本镰仓时代,建立了以武士阶级为基础的武家政权,史称幕府。这个时期的文学,一方面充满没落贵族之感伤情调,一方面又充满厌世的无常观。
到了室町时代,「空寂」、「幽玄」成为此时期的文学精神,伤春悲秋调子更浓,并强调「心」的作用,把「空寂」和「幽玄」推至禅宗所主张「无」之意境,追求「无心之感」,欲达至「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超越意识的幽玄境界。即使中国南宋时传入日本的水墨画,日人亦融贯空寂的艺术精神,在画面留下大幅「留白」,仅让人以「无心之心」去感受、填补和充实,去体会那没有绘画出来的东西和美丽色彩。这点很可能启发了柴田炼三郎,加上禅和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使他为笔下人物构想出「心中有剑,手中无剑」之玄幻武功,该武功叫「无行的架虚」。
使出「无行的架虚」,须以平静心境、无形架势亦即招式,去求取胜利。架势,是天地中阴阳五形。古传把架势定为阴阳二者,心中之剑即是——阴之架势有阳之变,阳之架势有阴之变。外实,内必虚。心为架势所拘者,必败。必胜不在于架势,而在于心之正。
吉川英治武道大讲「开悟」和「无隔」。他笔下东洋大剑客以禅印剑、以剑参禅,最后达致「剑禅合一」的「真空一剑」,剑客应取剑道而舍弃爱情才是生命的至高境界等等。这令柴田炼三郎十分欣赏和在作品中融会贯通。柴田的《决斗者宫本武藏》一书中,就一再提到「心法」和「剑法」的极致都是「无」。
古龙更是把这种空灵剑术理念发扬光大、青出于蓝,再加上一股迷人的「凄绝的杀风」,这成为他笔下高手的至高之境及吸引读者的必杀术。该「空」、「无」至境,使侠者从个人小空间进入大自然的大空间,从「有限」进入「无限」。在契合柴田「必胜在于心之正」理念上,古龙在《楚留香》一书中,就曾借李玉函之口道:「心正则剑正,心邪则剑邪。」另又有西门吹雪说的:「唯有诚心正义,才能到达剑术的巅峰,不诚的人,根本不配论剑。」而西门吹雪的剑术也达至「无人、无我、无情、无剑」境界。
香港影评人石琪曾评说古龙道:「古龙的天涯明月刀虽已消失,但流星蝴蝶剑的想象,仍能引起浪漫的共鸣。古龙小说的特点,就是保留空白,让读者与导演有着自我想象的余地。」
古龙为人津津乐道的「无招之招」、「手中无剑,心中有剑」之物我合一的武术最高境界,原创人是否应为吉川英治和柴田炼三郎呢?
再根据日人所追求的「无心之感」,被东瀛武侠小说家转化为日本武侠特有的「空相」和「无相」艺术象征,柴田笔下的眠狂四郎手中之剑就叫「无想正宗」,也许,这也就是后来台港武侠小说家古龙等包括影星周星驰,也在电影中大玩特玩的所谓「无相神功」吧。
柴田和古龙笔下人物大多潇洒诡奇、武功儒雅。眠狂四郎的「圆月剑法」悲情凄绝、无暇可击。其剑法是以剑尖绘出一个大圆月形,招式扑朔迷离,但一招见效。请注意,当他手中无剑时,他甚至「以手代剑」出招,也同样成功。
「小李飞刀」天下闻名,但日本武侠小说家丹下佐膳写的《独臂剑魔》内有一「飞刀矮人」豆太郎,身怀飞刀绝技,飞刀一出:「空中飞翔的鸟马上会堕地,水中遨游的鱼很快白肚上翻、浮出水面。」村上元三的《佐佐木小次郎》中,也有懂忍术擅使飞刀的女贼樱樱。柴田笔下的女神偷阿龙也使用神乎其技的飞刀。
也有人说古龙的「小李飞刀、例无虚发」,是受到他崇拜的郑证因「子母金环、出手双绝」的启发。而台湾著名武侠评论家叶洪生大哥则认为,古龙应是受到王度卢在《铁骑银瓶》一书中,写「病侠」玉娇龙恶夜歼敌等故事而获启迪,模仿形迹最明显者,当推李寻欢与玉娇龙二位「病侠」,皆是一边咳嗽、一边放暗器且「百发百中」的。
古龙的「小李飞刀」,有否受过其它小说家或柴田炼三郎的启迪呢?
柴田在《决斗者宫本武藏》的「宝藏院众徒」一章中,宫本武藏比陆小凤更早使出那招百战百胜「灵犀一指」的著名招式,而该招司马辽太郎也曾用过。
台湾作家司马中原在《湘东野话》一书中,描写大侠齐鸣泰能以手指神技「挟断」他人兵器。更有人认为陆小凤这种神功脱胎自王度卢《鹤惊昆仑》书中的高手。
那么,古龙的「灵犀一指」,又有否也曾在同胞作家或日作家中得到创作养份呢?
这一切,都随古龙的逝去而无法解答了。
然而,无可否认,即使飞刀绝技非古龙首创,但古龙写来更活龙活现、奇妙无穷,功力更在以上各人之上,使他的读者看了为之激赏非常。
写情写女人的高手和「色欲」描绘
柴田炼三郎和古龙同是写情写女人的高手,二人都写有不少这方面佳章。
柴田炼三郎擅写妖女和心理变态的妖妇、妖姬,如《眠狂四郎》一书专门下毒手迷晕少女在她们身上剌青,再把她们活生生剥皮的吉田城主千金,同书另一个专逼迫男人把她「引领至极乐世界」,然后把他们残杀的妖姬。惟是酒色之徒的古龙,因心境更为寂寞冷峻,对情和女人体会更深,所以写来愈见高明,最令人印象深刻是好些「人格在怨恨中扭曲,心灵在嫉妒中变态」的女子,较典型莫如《绝代双骄》里的移花宫宫主,《流星•蝴蝶•剑》里的高老大,《月异星邪》里的温如玉等。
柴田写妖姬一流,写至刚至柔美女也十分动人,而且他对女性的病态美似乎情有独钟,笔下不少美女不是脸色苍白、弱质纤纤、命途多舛,就是患肺病咯血而亡的可怜弱女。他写受了伤的美女美保代手掩伤口:「那褪成蜡色的美貌,白唇微微抖动着……」这令铁汉眠狂四郎见了,亦情不自禁感到哀悯。
无论柴田或古龙笔下男主角如何孤独、如何空虚寂寞,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往往有不少死心塌地爱上他们,且深陷情网而无法自拔的女子。柴田笔下如源四郎身边的美音、丝耶、广姬;主马之介身边的千草、美尾姬、朝路;梦殿转身边的清姬、千枝、加枝、琉球公主;还有宫本武藏身边的阿幸、夕姬、夕加茂等。古龙的以楚留香最厉害,身边除了固定照顾他的李红袖、苏蓉蓉、宋甜儿三女之外,还有张洁洁、艾青、华真真、西域龟兹国琵琶公主等众多美女。
但比较起来,古龙写美女则比柴田更胜一筹,他写的美人如沈璧君、林诗音、冰冰、思思、花月奴,无不令人印象难忘。其中《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林诗音也许脸色太苍白,身子太单薄,她的眼睛虽很明亮,却嫌过于冷漠,然而她的风情、气质则甚有东瀛女性的凄美气息。当然,林诗音毕竟是东方女子,请看古龙是如何高明地以张艺谋最擅长的强烈色彩法来写出尘脱俗的林诗音:
「她穿著浅紫色的衣服,披着浅紫色的风氅,在一片银白色看来,就像是一朵清丽的紫罗兰。」
「他记得那亭子的栏杆是红的,梅花也是红的,她坐在栏杆上,梅花和栏杆彷佛全都失去了颜色。」
事实上,古龙笔下写得最妙是一些「老女人」,她们虽然年纪已有一把,但仍旧美艳不可方物,如《萧十一郎》里的风四娘就很典型,本来「剌激最容易令女人衰老」,但风四娘「喜欢骑最快的马,爬最高的山,吃最辣的菜,喝最烈的酒,玩最利的刀,杀最狠的人。三十多岁的她,却一点也不显老。」
古龙的确写得很生动形象。
不同的是,因中日文化的歧异,中国人喜欢任何事都有圆满结局,好人得道,坏人恶有恶报。日人小说及戏剧很少有大团圆结局,扶桑观众可以潸潸泪下地看着舞台上男女主角惨遭悲剧终场,却不会感到不满,反认为是合理的,这正是一夜娱乐的高潮。也因此,柴田所写人物最终不是妻离子散、浪迹天涯,就是决战失败、死于非命,基本上没有一个好下场,宫本武藏因和徒弟决斗,且成为痴呆。而古龙所写人物经历大灾大劫后,都能打败恶人,逃脱恶运和找到意中人,获得幸福。不过他的《萧十一郎》,却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悲剧,他以感人的笔调,写来至情至性、敢爱敢恨,但又不同于柴田的煽情,更不同于王度卢的悲剧侠情,他比柴田和王度卢高明的是除了男女感情的哀怨缠绵外,还有对高尚人格的讴歌和对欢乐生命的热爱。
日本女性地位是低下的,台湾被日本长期统治过,文化社会风俗都受其很大影响,所以柴田与古龙都很少写及如金庸笔下武功高强、能独当一面、在男性社会处主导地位的女侠。
还有一点和金庸、梁羽生等武侠作家很不同的是,无论柴田或古龙,都写及较多和较露骨的「色欲」与「性」。日本人并不忌讳性事,民间男女婚嫁时,家人会给他们「枕草纸」和详细描绘性交姿势的图画以习学,社会上男女婚外情更是普遍化。日人认为:「不好色者,犹如玉杯之无底,在人格上存在根本性缺陷。」井原西鹤名著《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中,就极尽描绘男女情欲性爱。《金阁寺》内的寺院主持,可以公然召妓,纵火的主人公且把女人的乳房幻化为金阁。
日本民族可以用坦然、率真态度去面对这种「人之大欲」,却不会令人觉其猥琐,这是因为日人对「性」根本持开放态度,「好色」一词,不外指男女之间的痴情和相互爱恋而已。日本神道对性爱亦采取宽容态度。即如有人认为同是写皇族生活和对爱情点染着墨的《源氏物语》乃日本的《红楼梦》,但《源氏物语》比《红楼梦》更多了通篇靡逸诲淫和男欢女爱描写,源氏公子的诗不离「爱此合欢榻,依依不忍离」,与宝玉典雅诗风大异其趣。
故此,柴田作品中,充斥着同性恋、性变态、自恋、自虐、虐待狂等情节,书中不乏对女体甜润柔美的描写。他的《决斗者宫本武藏》一书,孤傲的世外高人,为了同情战后寡妇,竟公然对其「遍施雨露」,甚至有大剑客毫不忌讳地自称本身以手淫来解决性欲的。
有人说古龙笔下男人过于好色,女人则对性太过随便,不但动辄「嘤咛」一声主动倒在男人怀里,而且喜欢在男人面前宽衣解带、一丝不挂,这在中港武侠作家中都比较少见,而台湾女作家多年来流行「情色小说」,大陆直至近年才有「上海宝贝」卫慧、绵绵小姐的「跟风之作」。其实「情色」正是日人特色。柴田小说充满女人和性,更有淫秽乱伦描写,大剑客不但有一夜情,(如剑客梦殿转因与公主一夕之欢,结果被幕府大举追杀。)还强奸女子。古龙笔下的楚留香和陆小凤等男主角亦有一夜情,对女性也喜调侃取笑,并非金庸笔下那种非礼勿视的正人君子大侠,但不可不知,古龙笔下男女之间不少具感人真情,他比柴田超越的,还有境界的提高和对人性深刻的描绘,
以下,可看看二人于这方面的描写,以作比较。
柴田有关女人的佳句有:
(1)「不要为女人所救,再被其依靠终身。」
(2)「这就是女人吗?女人爱上男人,能下决心赴死。我即使爱上女人,也无法为该女人赴死的。」
(3)「眠狂四郎是个杀伐的人,对于敌人的来临,有如文人墨士对季节的敏感……比起美保代那世上罕见的美貌,他更爱虚无的孤独。」
(4)「男人追女人时,她一定逃。女人追男人时,男人也一定逃。不过,冤家路窄,迟早会碰到一起的。」
古龙的有:
(1)「美人和好马通常都是难忘的,好花多剌。」
(2)「等她也如梧桐叶子般凋落时,还能怀念她的人,又有几许。」
(3)「感情有时候非常温和的,有时却比刀锋更利,时时刻刻都会在无形无影间令人心如刀割,只恨自己为什么还没有死。」
(4)「钱这种东西,就好象女人一样,你追她的时候,她板起脸不理你,你要推她的时候,推也推不了。」
带两分邪气、不羁、不快乐的酒徒和浪子
古龙是浪子,是酒徒。林清玄说当年去他家,总见到满架的酒。他爱酒,犹如他笔下人物西门吹雪的爱剑,已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最后终以身殉酒。他性格有着诗人的敏感和浪子的空寂无奈,犹如古代侠客走错了时光隧道,故此冀能一大醉而浑忘众生。
他曾经说过:「我也曾是酒徒,我也曾在生死间来去,如今虽然自甘寂寞,远避山上,但却时常会有些身不由己的悲哀。」
他又说:「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根的浪子,身世飘零,无亲无故,他能有什么?」
古龙小时常爱手拿竹片木棒,拼命追打邻家的鸡鸭鹅,吓得附近的家禽见了他都不敢任意近前,但某次还是把邻家一只鸡打死了,害他娘赔了好几块钱,结果被娘亲狠狠痛打一顿。
他还爱扔石子,被街头顽童称为「石头王」。又爱弄刀,收集了种种式式的刀,百般摆弄,并和台北市大龙峒、西门町一带童党及横行大台北的五路把兄弟,在路摊边喝老酒,边谈刀经,引来四海帮陈帮主不以为然,要找他晦气,派出两个媚态撩人的小妞色诱古龙,古龙果然上当,被四海帮牛头马面左右护法押送帮主发放,幸好古龙嘴头了得,二人一见如故,陈帮主非但放人,且和气收场,数十帮众浩浩荡荡奔赴龙山寺夜摊喝老酒庆祝一番。
可见古龙的好色好酒,从小已见本性。
他自己也说过,当别人还正「背着书包上学去」的时候,他已经「落拓江湖载酒行」了。
在香港时曾到倪匡赛西湖的家,他告诉过我说,他和古龙最老友,去台湾常泡在他家中,两人彻夜谈文论道,斗酒谈女人,醉了就满地打滚相拥痛哭互诉寂寞。
柴田炼三郎笔下所写咯着血,脸色苍白病态但武功高强的东瀛剑客,月下白衣如雪、飘然脱俗,然内心悲苦、身世堪怜,脸上常闪现凄怆冷笑,如古龙李寻欢式被刻骨铭心相思噬食心灵故不快乐的浪子,是否曾很深地触动过古龙那一颗诗人敏感的心呢?
《决斗者宫本武藏》一书中,主角宫本武藏是雕刻高手,常以木块雕刻各种佛像以排遣愁绪。古龙笔下的李寻欢一出场就正在雕刻人像,只不过他雕刻的是他最心爱的女人而巳。
古龙有否借助柴田所写「雕刻」这种动作和道具呢?
古龙本质更像一个诗人,文字有种朦胧的、诗意的美,而他本身既是浪子,因此笔下所写浪子性格更见深邃苍凉,如大盗萧十一郎、快剑阿飞、探花小李、杀手孟星魂、侠盗楚留香、剑神谢晓峰、快刀傅红雪,其奔走江湖愁绪满怀又潇洒自如,虽然更多时是黯然神伤,十足十的江湖浪子。
本身是酒色之徒的古龙,写起浪子应是更得心应手、扣人心弦的吧。
他笔下那些没有根的浪子,只要得到别人一点点真情,就永远也不会忘记。但他们往往是内心沉痛的、不快乐的人。
像李寻欢,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不快乐的浪子。别人很难了解他,而别人愈不了解他,他愈痛苦。文学评论家曹正文指出:「小李飞刀李寻欢是个悲剧人物,是『一曲悲歌中的英雄侠士……』他总想摆脱孤独,总想与寂寞脱钩,于是故作洒脱,故作放浪,其实他心底里仍然无法排遣这种离情愁绪。」此外,像谢晓峰、西门吹雪、叶孤城、花无缺、萧十一郎,无不如是。萧十一郎更自比为一条狼,在荒凉的山野间徘徊,无家可归,守望着天明……
很多人以为楚留香是个风流快活人,风流也许风流,但古龙说:「很多读者都认为这个人是可以令大家快乐的人,可是在我看来他这个人自己是非常不快乐的。」
他在《飞刀,又见飞刀》中又写道:「在一个没有月也没有风的晚上……已是腊月了,院子里的雪已冻得麻木,就像是一个失意的浪子的心一样,麻木得连锥子也剌不痛。」文字非常感人。
而日本风情,正是东方伤感与凄迷之美的极致。古代日本「物哀」文学发展过程中,渐渐形成一股「空寂」和「闲寂」思想底流。浪漫感人的物哀、幽玄的空寂以及风雅的闲寂,三种文学思想精神相通。其中著名俳句诗人芭蕉就曾有「风雅之诚」与「风雅之寂」的俳论,这都深深影响着包括柴田炼三郎在内的东瀛文人,造成柴田风雅浪漫又略带忧郁的风格。
台湾学者何怀硕先生曾说:「日本人的性格,也许来自人类最深重的一种自卑感。世世代代,似乎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机感。」
美国女作家露丝•潘乃德在她的作品《菊花与剑》中也说过:「日本人常常陷于忧郁与激怒交替的挣扎。小说的主角事事感到厌烦——对日常生活厌烦、对家庭厌烦、对都市厌烦、对乡村厌烦……人们是敏感易伤的。」
因此,在这种文化氛围成长的柴田炼三郎,作品中人物大多是不快乐者,他的小说总是洋溢一股贯穿全书的忧郁之气。古龙本身也是敏感易伤、不快乐的人,他作品同具此种风格,真是一点也不奇怪。
柴田曾以如此文字形容他笔下人物眠狂四郎:「在那酷寒寂静得似乎用针一剌也会龟裂的夜气中,突然传出一声宛如野兽被压扁的怪异惨叫。」
武功高强、孤傲独行的眠狂四郎,并非冷酷无情之人,他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但却常以野兽般惨嚎,来抒发排遣内心的痛苦与空虚。
另一个主角源氏九郎则:「不知有多少次感到无比的孤独而倒在床上呜咽的流泪。」
柴田和古龙所塑造的侠士和剑客,好些都是身不由己地陷身江湖,回首红尘时,空余感慨的、伤情的浪子。
二人所写的浪子基本上没有好结果。柴田所写的武士梦殿转,在九死一生惨酷决战中,杀死可怕凶残的敌人后,却感到:「在世厌之、亡后思之。」毫无胜利的喜悦,有的只是空虚与惆怅,最后,他拋却一切,回到那风雅快乐的故人旧居「无风亭」,和心爱女子一起,这已是浪子最好的归宿了。
还有就是,日人对事物看法并非黑白分明,这在其「菊花与剑」民族性中即见端倪。即使著名天照大神的弟弟——「速猛的男神」赤戋鸣尊,也是个具善恶两面的神,他经常搞恶作剧大肆捣乱,甚至把姐姐的房间撒满粪便,并投进被他「逆剥外皮」的斑驹,(即男性生殖器。)最终被放逐到「黑暗之国」,但他却是东洋人最喜爱的神。这可说明柴田何以常写神秘、怪诞、有黑暗和光明双重性格的剑客和武士。
而古龙也爱写亦正亦邪的杀手、侠士和浪子。
这些都并非金庸、梁羽生笔下传统「侠之大者」之正统大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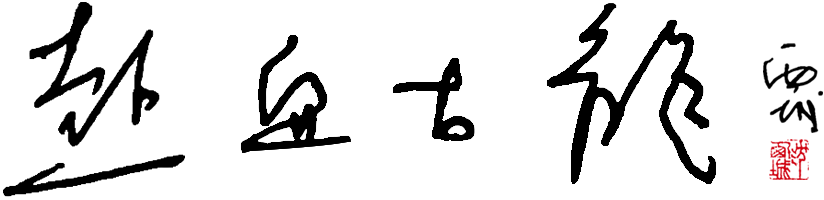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