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小波
二、文学性的自觉: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法革新
古龙的武侠小说之新,首先与一种写作上的技法革新有关,彰显出一种文学性。文学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也有不少具体的表征。首先来看,是一种叙事中所蕴含的抒情性,这与古龙本身的才情有关。古龙说:“一个人如果沉溺于酒,必定有他伤心的事,而伤心的人必定是多情的人。”这种情,既是儿女之情、人之常情,也是作家的才情。“情”成为古龙笔下核心的元素,与小说本身的叙事性形成了张力。“古龙无疑是写情的高手,他能深刻写出人间的种种恩怨。”[11]《多情剑客无情剑》是古龙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小李飞刀”系列的第一部,被公认为古龙武侠作品的巅峰之作和最高成就。这部作品的核心叙事要素为一个“情”字,多情与无情,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推力。这是一部阐明武学真谛的作品,也是一部写尽人间世态炎凉的人情历史画,武侠故事在情感的纠葛中展开。《萧十一郎》的主题也和情有关,萧十一郎原本过着潇洒浪荡的日子,在一次意外追逐中,卷入了武林传说中人人窥伺的神秘宝物割鹿刀之争,并因此结识了武林第一美女沈璧君,并开始了恩怨纠缠的一生,十一郎极度痴情,甚至为情所困。同时小说中还出现了另一个江湖奇女子风四娘,也极度重情,选择为自己的感情坚守。《多情剑客无情剑》
古龙采取一种极富艺术性的手法描写功夫与武打场面,被称为“武戏文唱”,这样更适宜自己情感主题的表达,也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格局。在古龙看来,文学是写情的一种最好艺术表现形式,而写好感情波澜,比写惊心动魄的武打更能扣人心弦。写江湖、功夫的同时,古龙还擅“言情”,刀光剑影中,儿女情长丝毫不逊色,有时候甚至盖过了江湖大义。这一方面使得作品更能捕获受众的心弦,另一方面也能最大程度体现出一种文学性来。
在技法上,古龙的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创造性地将戏剧、推理、诗性等元素带入传统武侠,又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融入其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古龙式武侠小说风格。古龙成功地运用了写景、写情、写心态的新派写法,又兼顾中国传统小说环环相扣、扑朔迷离的情节安排。阅读古龙的文本,在流畅性的叙事和情节的引人入胜之外,也十分讲究修辞学策略,艺术张力,起承转合,技术层面的保障。推理、悬疑等方法的使用则和现代技法的引入有关。有很多研究提到了古龙受到西方作家的影响,考察当时的语境,确实有多种现代文学思潮的引入,势必会对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古龙的写作多借鉴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写法,处处设置悬念,勾起阅读欲望。早期较为成功的作品《绝代双骄》正是如此,小说中故事套故事,悬念丛生、扑朔迷离,具有很大的可读性。语言上,古龙追求极致的表达,鸿篇巨制也不缺乏对语言的雕琢。小说语言经过精心雕琢,贴着人物,对话意味深长,往往蕴人生哲理于故事之中。《绝代双骄》将对话运用到极致,比如江鱼儿与苏樱的对话,在风趣生动的对话中,活现人物形象。古龙用短句、哲理、倒叙以及蒙太奇手法来构思情节,都给人一种面目一新的特点,赢得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广泛喜爱。《天涯•明月•刀》《流星•蝴蝶•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武侠标题,而是将三个意象并置,形成张力,充满诗性。《绝代双骄》
古龙在人物塑造上也十分成功,众多的人物个个形象鲜明,读罢之后在脑中挥之不去。这些人物性格豪迈,敢爱敢恨,同时又是充满着矛盾、复杂的个体,几乎都是圆形人物。在大的外部环境中坚守、变通,鲜明的人物形象,回味悠长。很多人物的名字都颇费周章。在《绝代双骄》中,整部小说气魄宏大,塑造了以江小鱼为首的一群成长变化中的人物典型。全书人物有名有姓的就有百余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和个性。古龙笔下的英雄如楚留香、李寻欢、陆小凤等,追求基本的江湖道义,仁义礼智信是他们的信条,同时也追求真挚的友谊、甜美的爱情以及充分的物质享受,并追求个体的自由,而这些,是每一位普通个体的生活信仰。他们是英雄,也是普通的人。《楚留香传奇》中的楚留香,是一个江湖大盗,但他“盗亦有道”,江湖中人尊称他“盗帅”。他为人风流倜傥,足智多谋,观察入微,善良多情,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盗贼。陆小凤系列中的主人公陆小凤,可以说是以追求潇洒为终极人生目标,也是活得最痛快的人,喝最醇的酒,过最刺激的日子,身边环绕最美的女人和最千奇百怪的朋友。小李飞刀系列的主人公李寻欢本来仕途得志,由于被胡云冀以“结交匪类”的名义上奏弹劾,以他淡泊名利的性格,终于辞官而去。由此他才能投身江湖,成为首屈一指的武林人物。人性的深度发掘自然和一般的武侠作品中人物善恶分明不同,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立体的、圆形人物,并不能贴上善或恶的标签,而是在社会环境的熏染中选择了各式各样的人生。多为矛盾的个体,或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或是被人陷害、受人要挟走向恶之途,或是机缘巧合无知地走向作恶,与传统的高大全的侠士迥异。
有一种通行的观点,认为古龙将通俗文学带入了纯文学的行列,其实不无道理,他的作品通常都是较为通俗的选题,骨子里面却十分注重小说技法。总的来看,古龙的小说是现代与传统一起浇灌出的果实。一方面,古龙遵循古典和传统,将民族基因承袭下来,循环时间观、悲剧精神。延续了文学的母题和结构,即盛-衰、聚-散、色-空、梦-醒的基本模式。考察古龙作品的结尾会发现,故事的大结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圆满,而多是释然、放弃、退隐。《天涯•明月•刀》《萧十一郎》等无一不是如此,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固有修辞模式,既有沿袭,也有突破。
另一方面,古龙追求现代表达,小说修辞运用自如,大量的现代技法引入。古龙的现代化,最为明显的是对现代生活的观照,“可以这样说,它是把现代人放进一个虚构的古代中去,但他的人物也不仅仅是现代人的影子。同时也包含着古龙对现代人的理解和理想小说主人公那种悠游自在的生活,就可以说是对具有强烈生活节奏的现代生活的否定和超越。”[12]古龙的武侠小说在细节上也值得称道,并不仅仅聚焦故事。古龙的“爽文奇观”建构与他所采用的现代化小说手法不无关系。虽然武侠小说有着中国传统的根基,但在写法上博采众长,吸收了诸多纯文学所采用的叙述技法,在通俗之外有了很强的文学性,古龙的文学才情很高,文学造诣也很好。古龙时期,正是中国文学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时代,西方文学和文艺思潮自然也会影响通俗文学的创作。
为什么大家都爱读武侠小说?赵毅衡指出,武侠小说体现了一种“全民共识”[13]。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核心就是一个受众的问题,受众面大就是这种“全民精神”“全民共识”所决定的。陈平原所说的“通俗文学中蕴藏着深刻而真实的社会无意识”[14]、李零所言的“武侠中有人类最基本的兴奋点”[15],都是这种全民共识的同义语,都反映了社会对人性自由的压抑,而阅读流行小说可以缓解压抑。[16]武侠小说对此发挥到极致,“爽文策略”使得欲望得到替代满足。更为重要的是,江湖人物所秉持的道义,及其所代表的一种全民共识、社会无意识、基本的兴奋点,都指向一种基本的审美要素和品格。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达到了某种耦合。武侠小说蕴含了一种文学传统和审美要素,符合阅读习惯,这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全民共识,这些特性在其他的文学形式和文本中也有体现,诸如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红色经典、莫言、余华的当代小说,体量巨大的网络文学,其实都有符合民族特性的审美基因。古龙的武侠小说具有“爽文”的一切特质,是读者“武侠梦”的替代满足。同时,作品中所蕴含的民间隐形结构与现代小说技法,又为文学性增色加分,武侠小说的经典化与文学史地位也正是在文本编码之初就已经奠定,随着接受环节而愈发巩固。
但是,古龙的小说似乎不满于这种共识的表达。这或许是古龙新武侠根本之新所在。古龙的新武侠,既有这种传承,也有对这种全民共识的突破,不断书写这种共识,同时也在反思并挑逗这种共识。古龙的作品既写出了这种人性,也在反思这种人性。既写出了一种民族精神和共识,也在不断突破这种东西。比如技法的精雕细琢也是在挑战一般的武侠小说共识。因为在常识那里,武侠小说越通俗越好。出于连载需要,通俗文学都是大部头的作品,但对读者来说并不觉得冗长,因为作品的审美距离几近消失,读者的阅读障碍几乎全都规避掉。即便在快餐文化时代,仍有广阔的市场,各种版本仍在市场上流通,出了一种武侠情结,还是和可阅读有关。但是古龙并不完全信奉这一点。对英雄的解构、对欲望的过分释放、对杀戮的痴迷、对功夫的醉心、对个性的过分张扬,都是他对传统武侠的修正。
当然,过分的挑战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主题上,古龙从外国小说中吸取现代意识和现代情绪,从“硬汉派小说”中吸取情节结构。在创新的过程中,古龙还做了很多的“修正”。这些“修正”使得古龙小说保持了“武侠小说”的基本性质,却也说明了古龙的创新思维隐藏着危机。这些创新的武侠小说看起来有了新的因素,丢掉的却是小说的“武侠味”。[17]又比如他对技法的过分追逐也导致了读者群体的不满,小李飞刀系列第四部《天涯•明月•刀》并未连载完,腰斩的原因后来被揭秘,多与受众的理解差异有关,“《天涯•明月•刀》连载於‘人间’副刊竟被腰斩,原因是许多读者不习惯古龙的快节奏,蒙太奇笔法,去函报社表示要‘退报’,吓得报社老板请出东方玉等武侠家连载,而中断了古龙的作品。”[18]“文风跳跃、读者大惑”正是作家的技法追求与受众需求的错位。还有很多作品中都出现了短句的铺排,也稍显刻意,这或许与作家本身的艺术追求与约稿方的催促有关,在一些时候反而不伦不类了。《天涯•明月•刀》
古龙笔下的武侠人物,大多风流成性,放荡不羁,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甚至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坏人形象,很多行为是世人所不齿的,这种写作,正是一种挑逗和挑战,而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样的人物形象。民族大义、家国情怀,这些看似公义的东西,却不断在遭受着挑战。所以,古龙的武侠小说会被归为新武侠。而正是这种只能在艺术中的对这种共识的突破,才会满足现实中不能实现的读者的心理需求,达到欲望的替代满足。这当然是所有艺术的奥秘,武侠小说更为突出。这也是古龙小说的革新表现,写共识,并挑战这种共识,这或许才是古龙新武侠真正新的地方。古龙的武侠小说传达出民族的基本共识与文学的基本主题,但同时,他笔下的人物在不断挑战这些共识。这是他技法上的成功,也是主题上的开拓。
三、主题流变:生命意蕴与悲情色彩
古龙对武侠之新开拓在主题上更加明显,在杀戮、功夫、武侠、传奇、快意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主题发掘。古龙的武侠小说在主题上是此前武侠书写的一种推进乃至颠覆。高位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便开始寻求突破和变革。在主题上也有所变化,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古龙武侠小说传统的快意恩仇中融进了更多人性的思考,更多的是一种生命书写和人生的悲情表达。古龙好酒,追求一种“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矣”的生活状态,其笔下人物也多是好酒之徒,“酒神精神”似乎天然和悲情联系在一起,微醺迷醉中,是“借酒浇愁”而不得的无奈人生。
古龙更加注重个体性,这与纯文学的演变脉络也比较一致。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新时期,主流文学都注重个性化的书写,文学的终极要义正是人的解放。古龙武侠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个体的强调,将传统武侠对家国宏大主题的重视移步至个体化追求上,将个体的命运流转作为核心叙事素。很多作品不能仅仅当作一个武侠文本,比如《浣花洗剑录》的故事从东赢剑客白衣人挑战中原武林群雄开始,以方宝玉的成长经历为线索,这部小说没有设置多少武侠小说惯常的道具,还舍弃了以往的“复仇”主题,融入古龙对生活真谛的理解,表现了对上乘武学和人生真谛的参悟,主要落笔处还是人的一种自我认知与觉醒。《浣花洗剑录》
古龙笔下的主人公大多具有鲜明的个性,追求自我的解放,豪放不羁、风流倜傥、我行我素等是这些人物的显著特征,“浪子心曲”是其作品的整体风貌,个性的解放与整个文学的转型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这种人的解放、个性化凸显中,作家写出了生命悲情性的一面。在命运的支配下,人物虽有反抗,但不得不妥协,生命的凋零与精神的妥协营造出了一种十分明显的悲情色彩。这与现代化进程带给人类对命运反思的悲剧哲学十分相似。
古龙早期的作品多喜剧的笔调,从《绝代双骄》开始逐渐由悲转喜,而后来的写作悲剧性明显增加,空无、虚幻、无奈、凄凉、惆怅成为主题。虽然他一再强调写喜剧,给读者以希望,但是他骨子里是信奉悲剧理论的,多描写美好事物的毁灭,人生的不得已,身不由己。如《英雄无泪》中的蝶舞,本是最好的舞者,但身不由己,无法面对自己的情感,最后自断双腿,不治而亡。命运的无奈性表达几乎贯穿着古龙的所有作品,这些人物,集肝胆侠义、忠贞勇猛、理想情怀于一身,往往对其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自由的追逐,社会的逼迫,很多时候做出了违背初衷的选择,或者犯下了自己并不知晓的罪过,陷入悲情的境地。
古龙的小说人物结局处理很好地诠释了这一主旨。虽然古龙的作品也沿袭了传统小说的套路,善恶有报,但是那些惩恶扬善的英雄人物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有着更深的追求。英雄人物最后的结局很多是退隐,写武侠,其实是写武侠的退场。这是一种悲观的宿命,也是聚散模式的终极演绎。《苍穹神剑》的结局,主人公熊倜误杀红颜知己,在复仇之后选择自杀。《天涯•明月•刀》讲述了江湖名流公子羽,诱惑燕南飞做自己的替身,并派遣他去刺杀傅红雪。傅红雪两次战胜燕南飞却没有杀死他,他拒绝学燕南飞一样担任公子羽替身,离开那些诱人的财富,只是回到一个真心爱他的女人身边。而公子羽也意识到继续下去是不行的,便放弃了名利,退隐江湖。《浣花洗剑录》的最后,主人公一死以求得武道真谛。《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最后的结局也是退隐江湖。争斗与杀戮的最后,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心安。这种结局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是一种刻意安排,与人生的残缺关联起来。
“一直以来,古龙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上‘求新、求变、求突破’,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在‘大武侠时代’写作中,不仅寻求文字技法的凝练和奇崛,更期望除了‘武侠’固有的传奇性,更能注重日常生活的书写。”[19]正是这种日常生活的书写,让他的写作一下子从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回到每一位普通个体那里,从伟岸的英雄到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何尝不是另一层面的“新武侠”的表达呢?古龙的成功,和中国深厚的武侠文化根基、文学影视文化的联姻等原因密切相关,但更为主要的,依然是古龙本身的文学才情。古龙的武侠小说取百家之长,归根结底绕不开文学性,纯文学写作中也大抵如此。比如古龙的小说也有对国民性的反思批判,一种启蒙的情怀也蕴含其中。作品对人物性格的缺陷、弱点,甚至丑陋的一面也多有揭示,是一种反思性的书写。在古龙小说深处,推动情节发展的往往是个体的各种情绪,如《名剑风流》中既有兄妹乱伦,又有婚外偷情,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尽在其中,古龙正是将这些人性中贪、嗔、痴所引起的非理性的心理行为都勾勒了出来,构造出一个疯狂的世界同时,他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和婉转的曲笔,批判了那种前代仇怨化为现世业报的伦理模式,并塑造出充满人性和人情的新一代江湖人物。
近年来,文学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也逐渐被主流文学所接纳。特别是金庸的引入与流行,声势浩大的“金学”引发了关于通俗文学经典性的思考,不过,通俗文学的成就又岂是金庸一个人可以担当的,漫漫长路上有一大批人参与其中,孕育出了影响深远的通俗文学。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典型代表,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鸿沟一向很深,虽然近年来的学界对金庸、古龙等人的通俗小说的经典化地位认识有了明显改观,主流文学史也将其纳入讨论,学界发出了较多的声音,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创作体量和读者群体,这些关注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不少研究都将通俗文学作为一个现象进行整体的考察,很少落到具体的作家和作品上,尤其是对文本本身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仍是短板一块,而这些文本,其实大有玄机,值得细细研读,仅从这一点而言,通俗文学研究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注释】
[1]古龙:《古龙代表作大全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2]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4]吴秀明、陈洁:《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
[5]林遥:《折断刀锋——古龙的“大武侠时代”》,《天涯》,2022年第3期。
[6]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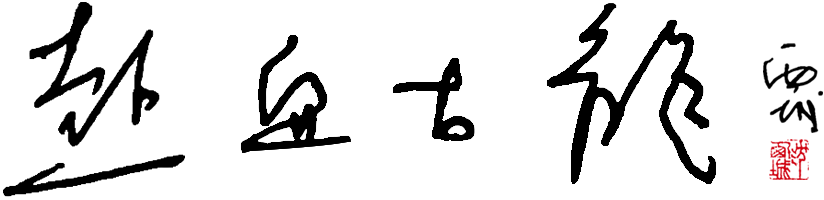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