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尧吉
二、乌合之众
在金庸、司马翎、卧龙生、东方玉等人笔下,往往充斥着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群雄”(或“群豪”)。这个群体的成分十分复杂,既有来自三山五岳的名门正派,也包含来自五湖四海的牛鬼蛇神,更兼有出自绝域边陲的奇人异士;从老到少,从雌到雄,无论是高手低手,正派反派,均无所不包。在金庸大多数的创作中,这个群体时常会为了一个奇怪的目的聚拢在一起,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所过之处鸡飞蛋打、人仰马翻,无人能制止其中的癫狂。
比如《笑傲江湖》中群豪扯旗擂鼓,拥戴令狐冲去少林寺救任盈盈的那一节,群体的幼稚盲从和甘于受虐的心态便令人发指:只不过因为从前奴隶主老大东方不败扣发解药时,身为奴隶主老二的任盈盈略略讲了几句好话,群雄便忘了被迫长年服毒和受奴役差遣的苦痛,也忘了不久前只因不小心看到任盈盈私会情郎的隐私便被罚以自废双目、流放荒岛终生的荒诞,而殒身不恤地去围攻少林虎穴,结果不仅饱尝铁钉穿足利箭穿身的滋味,还丢了至少数十人的性命。
尤为可笑的是,令群雄自作多情的任盈盈身为高级人质,却在少林寺享受了宾客般的优待。她获释后,感谢的也根本不是前往枉死城的好汉们,而只是有情有义的冲郎。
从某方面来说,群雄和任盈盈间的这种关系类似于关起门来SM,本不需局外人来说三道四,但令人心寒的是,群雄对任盈盈温情脉脉的另一面是却对其他平民属群的残暴无情。《笑傲江湖》“围寺”中,数千群雄在少林寺随地大小便虽亵渎了佛门,却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方正和释永信两位大师当然要添堵和不快,但毕竟雇些人打扫后便可重新开张。而在上嵩山前,“接连数日,(群雄)都是将沿途城镇上的饭铺酒店,吃喝得锅镬俱烂,桌椅皆碎。群豪酒不醉,饭不饱,恼起上来,自是将一干饭铺酒店打得落花流水”,金庸也没提赔偿一事:多半是没有。如果我们是店主,万一更不幸还是该朝下岗人员,那么我们不仅要对死伤的群雄暗自说一声“报应”,对令狐冲英雄救美的所谓江湖佳话也多半竖起中指。
群雄聚集,脑残遍生——金庸江湖里的这些群体行为很难用常理和逻辑来解释,压倒一切理性的狂热和盲从是其基本特征。一百多年前,法国人勒庞便曾在《乌合之众》慨叹:“面对群众的荒谬与狂热,明智之士更有可能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努力,而是同群体一起陷入其中,事后又惊叹于自己连常识都已忘却的愚蠢……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
在《笑傲江湖》中,金庸便提到“其中也有若干老成稳重之辈,但见大伙都喜胡闹,也只有不置可否、捋须微笑而已”;而在《天龙八部》的聚贤庄大战中,金庸又提到群雄中不少有见识的人其实在琢磨:“也并非只要是胡人,就须一概该杀,其中也有善恶之别。那么契丹人中,是否也有好人呢?……乔峰未必是非杀不可,咱们也未必是全然的理直气壮。”但个体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任何睿智、理性、见识就轻易被吞没。在嵩山派和乔峰的犀利反击下,被裹挟在群雄中的理智者与盲从者一并玉石俱焚。
换在正常情况下,“黄河老祖”等人根本没可能产生挑战少林的冲动,湘东的向望海和关西的快刀祁六也很难说会有向乔峰递刀子要求单挑的勇气。但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个体一旦加入群体后,他往往就能获得虚幻的勇气、自以为是的力量和法不责众的安全感,特别是某种随心所欲处置他人的权力快感——想当年乔峰那厮仗着“北乔峰”、“丐帮帮主”等旗号牛X闪闪的连正眼都不愿意瞧一下自己,如今却不过是一条走投无路的落水狗而已!《乌合之众》的某句话几乎就是乔峰一生命运的谶语:群众会把末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
而《连城诀》中,群雄的群体心理尤值得玩味,金庸以其妙笔将一支正义之师如何发端、衍变、癫狂直至崩溃的过程刻画得入木三分。
事情从血刀老祖掳掠水笙说起:因血刀老祖好色劫持水笙,一开始只是水笙的表哥汪啸风率人来救,其后水笙之父水岱等“落花流水”南四奇加入——救援队伍此时还只限于血亲等小圈子。但随着血刀老祖逃亡路线的拉长,追击的群雄队伍迅速壮大,湖广群豪、中原好汉、川东川中武人的加入使得最终追赶人众“已逾二三百人”。人员的身份也渐变得复杂,或为捕头镳客,或为著名拳师,或为武林隐逸,或为帮会首脑,甚至还有一名精于追踪术的关东马贼。
群豪的动机则五花八门:南四奇和汪啸风是为了援救血脉亲人;中原群豪却是动了公愤,认为若不将血刀门这老少二恶僧杀了,所有中原武林人士脸上无光;之后的四川武人虽与此事并非切身相关,“但反正有胜无败,正好凑凑热闹,结交朋友,也显得自己义气为重。”而那位总能发挥关键作用的马贼出于什么目的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晰的:一旦他加入了这个目标正义的集体,他之前的道德瑕疵和罪愆显然是被众人宽恕和忘却了。
然而追击血刀老祖的群体意志却随着情境的发展逐渐变得暧昧起来,不仅血刀老祖的武功和凶狡残忍令人胆寒,其后追进大雪山区域,恶劣的地形气候也导致群雄中有人心生怯意、借故落后直至溜之大吉。剩余的群雄虽因面子等问题不得不死撑,但游戏显然快玩不下去了,幸好最后来了一场大雪崩解决了这个困局:既然血刀僧师徒二人恶贯满盈终于被老天爷收拾,大家也可以结束这该死的追踪而凯旋了。
在《连城诀》一书中,金庸对人性之恶作了无以复加的描绘,群雄追击血刀老祖的某些细节正好与“逆反的群众”相契合。这“逆反的群雄”所持的残忍心理令人印象尤为深刻:从雪崩中逃得性命的群雄,大难不死后的第一反应却是“谁都庆幸逃过了灾劫,为自己欢喜之情,远胜于痛惜朋友之死”。如果说这还是出于人本能,另一些人在侥幸之余却想到“南四奇和铃剑双侠这些年来得了好大的名头,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死得好,死得妙!”
由此观之,群雄同仇敌忾追击血刀老祖的集体心理在最终的崩溃,远不止是因为一个共同目标消失这么简单。之后冰雪融化群雄重回雪谷,被狡猾的花铁干轻易蒙骗而群情激奋地诬指狄云水笙为奸夫淫妇并欲除之而后快;以及再后来为争夺天宁寺藏宝集体疯狂和毁灭,这个松散的群体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始终自大、个体的始终盲从及自私残忍都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在金庸很多作品中,群雄聚集在被加上胡汉相争的历史背景后,又时常能表现了很高的道德水准,舍身成仁的个体层现不穷。除雁门关为救乔峰而牺牲的群雄外,其他如追随陈家洛营救文泰来和掳掠乾隆、追随袁承志杀清兵抗击西洋大炮、追随郭靖杨过张无忌等迎击蒙古人、追随肖半和劫夺清廷朝贡鸳鸯刀等,其中师出有名以及建立在驱除鞑虏、恢复汉统立场上的道德自信不言而喻,基本呈现为正面形象。
但阅世愈深,反思必定越切。《天龙八部》中群雄围攻萧远山乔峰父子、《鹿鼎记》最后一节天地会群雄追杀韦小宝等,群体的嗜血和盲目便一目了然了。特别是《鹿鼎记》中,能把天地会群豪中的大多数个体玩弄于股掌之上、呼风唤雨且运气极佳的韦小宝最终却被这个群体逼得走投无路而不得不退出江湖,彰显了我族文化体制下某种不可战胜的“集体暴戾”。
其实从最近金庸修改《碧血剑》的一些文字,也可管窥其世故人心的暮年变化。
长久以来我曾对《碧血剑》结尾某些配角的人生选择有所怀疑,认为情况未必能像老先生想象的那么乐观:……(袁承志)当下率领青青、何惕守、哑巴、崔希敏等人,再召集孙仲寿等“山宗”旧人、孟伯飞父子、罗立如、焦宛儿、程青竹、沙天广、胡桂南、铁罗汉等豪杰,得了张朝唐、杨鹏举等人之助,远征异域,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别人且不说,孟伯飞作为家财万贯、门生遍地的黑道大豪,未到穷途末路而愿意舍弃中原花花世界和若大基业,陪这个只顶着 “北七省绿林盟主” 煞有介事大帽子的小青年远渡重洋去披荆斩棘、从头创业,是不大容易说的通的。毕竟老孟和袁承志并无甚过命的交情,早些时候还对袁承志被推举为盟主一事耿耿于怀,只在袁送了他白玉八骏马和翡翠玉西瓜等名贵珍宝贺寿后才改颜相向——以这些贪恋权、财的细节而言,孟伯飞岂能是浮槎于海之人?随便翻检明末清初的史载,踊跃成为两朝领袖的又何止钱谦益三二子。
而近来老先生修订旧作,不仅撤下了孟伯飞,连沙天广也拿下了,这显然是深思过的。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折服群雄的,从来就不是坚守道义立场的少年英雄,而时常是刘邦、朱元璋这类的铁腕枭雄,或者是任盈盈这样能使其陷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圣姑”。群雄只慑服于强人,他们虽喜好用虚幻的道义之名讨伐他人,但其实自身对道义规则不屑一顾,而与之对抗的个体如落单了,就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早期的古龙限于笔力和眼力,便时常为“仁者无敌”之类的童话所迷惑,典型如孤星裴玉,不通权谋之术、仅凭一颗赤子仁心便能老少通杀,感化收服绿林道上的各路凶狡之辈,文人的一厢情愿和意淫未免太过明显。
不过以古龙阴郁敏感的天性及坎坷的早年经历,他对宏大叙事的江湖从来便缺乏热情:《绝代双骄》、《大旗英雄传》中群雄集会,所图的大事不过是一起挖山洞救人而已。从《浣花洗剑录》、《武林外史》等开始,群豪聚集的口号喊得越响亮漂亮,其所作所为就越龌龊不堪,诸如诬指李寻欢和阿飞为梅花盗的正义庄群豪、陷害萧十一郎为卑鄙凶手的武林诸君子、合力围剿傅红雪的公子羽部下等等。
但与其说古龙对集体道德天然缺乏信任,不如说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个体在集体的威逼下如何坚守个人信仰和道德律的问题。那些个体的内心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中变得强大无比,任谁想强行成为他们的精神导师都是一个笑话,阿飞便曾对“最伟大的朋友”李寻欢过多侵入他的个人精神领域发出过怒吼。
在《边城浪子》一书中,古龙曾借笔下人物之口探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怎样看待阿飞这个人尤其是他的价值呢?易大经之流避之如蛇蝎;丁灵琳视其为传奇偶像;叶开表面虽尊敬他但内心其实认同丁乘风的评价:阿飞太孤独太骄傲,“是个永远也做不出大事来的(个)人”。而阿飞自身呢?
——他只认同他是这个江湖中的一个陌生人而已,尽管他有改变这个江湖格局的力量。与他同时代的群雄应该庆幸的,这样一个强人居然没有成为他们的领袖和牧人!
金庸笔下的那些个体英雄就甚少成为独行者,他们即便不是武林的宠儿,至少也和群雄打成一片,再不济也会有个帮派集体作为依托。所以金庸笔下的个体悲剧往往发生在他对自己所立身的集体感觉道德幻灭之时,这也是金庸创作中一个永远难解的“局”:他既清醒于宏大叙事的虚幻、群体的暴戾和个体的虚弱,但又必须给他的个体英雄设计一个箱金伴美、归隐田园的稳妥迷梦。
所以除了乔峰外,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能像古龙笔下的傅红雪、萧十一郎、谢晓峰等人,成为全民公敌,进入一个个体对抗整个江湖的困局并突围;但即便是乔峰,也不可能像古龙笔下的独行者一样,最终解开心中的枷锁,如同羽翼长久蒙尘的鸟儿一般涤尽血污,摆脱无知和残暴的牢笼,飞向无可羁绊的自由之地。正因此,我称金庸的那些个人故事为“一个人的遭遇”,而古龙的那些故事为“一个人的战争”。
回到乔峰,这个被群雄报复至毁灭的末路英雄,其实是很清楚用什么手段来有效对付这个表面看似强大却实质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的——最终能消灭暴力的,必然是更强的暴力。阿紫和耶律洪基便都直截了当向他建议:“姊夫,丐帮不要你做帮主,哼,小小一个丐帮,有什么希罕?你带领人马,去将他们都杀了”;“兄弟,你所以铸成这个大错,推寻罪魁祸首,都是那些汉人南蛮不好,尤其是丐帮一干叫化子,更是忘恩负义。你也休得烦恼,我即日兴兵,讨伐南蛮,把中原武林、丐帮众人,一古脑儿的都杀了,以泄你雁门关外杀母之仇,聚贤庄中受困之恨。”
然而乔峰变为萧峰不仅是姓氏符号的变化而已,来自中原的“维护汉统,尽忠报国,杀身成仁”等文化理念早与其肉身融为一体,他不可能以抹杀良知的铁血方式来报复群豪们。如前文所述,在乔峰的认知格局中,他始终找不到精神上的解脱之路、解不了族群归属的人生死结、摆脱不了被所有群体抛弃的恐惧,在他肉身最终毁灭之前,作为个体的精神其实已经崩溃了。读者无从苛责他,因为真正击败他的既非任何一群人,也不是玄而又玄的宿命,而是将之同化的某种文化心理。
王度庐《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也是陷于自身族群的宏大责任而无法自拔,无法超出“他们的时代”给他们设定的认知格局,最终以悲剧命运收场。作为个体的他们越强大,这种对抗命运的无力感就越突出。而《连城诀》中的狄云,虽然武功已经天下无敌,但是其见识心胸气度均不能脱离一个乡下少年的窠臼,宏大叙事约束不了他。他最终选择了雪谷苦寒之地以远离人群,读者也完全可以想象其今后必然是秉持淳朴本性生存——于江湖无害也无益,于其个人则是徒增年齿。如果他和水笙做不好节育措施,将来想必还要为儿女生食操心,毕竟大雪谷是很难养活一个大家庭的。
像乔峰、玉娇龙、岳飞、袁崇焕等个体命运的困局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永不停歇的循环,因我们这个族群的狂热永无消退之时。以至文化大师们不得不慨叹我们族群的血液中天生就带有某种狂乱因子,每隔几十年就要发作一次。而袁承志、狄云、令狐冲、韦小宝等的命运出路便是传统文化永远依赖的精神药品,只是文化人自身往往难以掌握好退隐的时机——即便今日,他们也不敢说自己就能幸免于彭德怀等人不久前遭遇的可怕命运:道德在踞兼真理在握的集体组织仍然强大和自信无比,并在审判个体命运的过程中始终拒绝给予个体平等对话的权利。
自然,乘槎出海、啸傲异域山林的人群也就日渐增多。在从前的江湖里,袁承志等悲愤去国者和被赏善罚恶使者牵引出海的中原群豪或都出于某种无奈下的选择,但如今他们的队伍中却加入了这样一群最精乖最狡猾的人:他们彻底放下几千年来培育的道义包袱,敛聚巨额财富后欣赴不归的异域,在指点父母之邦烟尘滚滚中的乌合之众时,嘴角露出得意和怜悯兼有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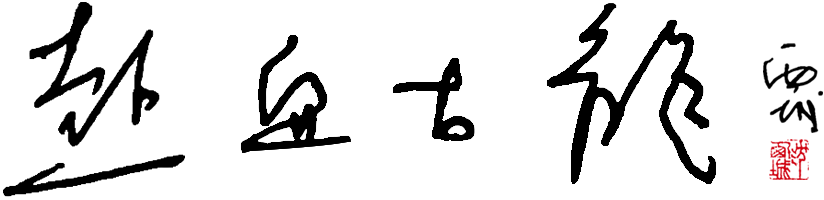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