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尧吉
三、圣君
率海之滨,莫非王土;溥天之下,莫非王臣。
这简简单单十六字,道尽了国家权力无限的历史渊源。中国的君王不仅掌握了全部资源,而且对人的生命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只要坐了那个位子,不管是圣贤、白痴,黄口孺子、孤寡妇人,皆能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其余的个人无论是如何杰出的才士,唯有匍匐称臣的份,所谓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辛亥之后虽王权消亡,但“上头”的权力仍日大。率海之滨,莫非国土;溥天之下,莫非党民。党国合璧,无论走的是左中右路线,训政均始终不变。
然而为何一定要尊王而不能民治民享?这观念的起源是难以解释的,只能归之于我族文明的“路径选择”。而后“奉天承运”导出的两个“莫非”,已然断绝了一切辩论的余地。近代的革命领袖也曾提到打破历史定律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来监督权力,但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一句空口许诺而已——所有人都可以被打倒,唯独他用权不受监督。“两个凡是”和两个“莫非”在骨子里是一致的,也断绝了一切说理的余地。
尽管历史证明,世俗权力唯一无法彻底根除的就是人的自我精神,但强人们始终在进行着从根本上摧毁民众对自治的信心和努力。他们或联合或收买掌握知识的精英群体,以说服民众服从,直至塑造他们甘为螺丝钉的性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经各代圣贤构建,君父至上、长幼有序的文化格局几乎坚不可摧——这也构成了君主威权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来源。当然,君主的卡理斯玛特质总是随着王朝的延续而逐渐衰减的,开国之君英明神武,其子孙却只能依照体制的惯性进行统治,在王朝的末尾更往往沦为暴君。暂时被驯服的民众揭竿而起成为暴民,其中的枭雄之辈更脱颖而出,窃据政权,毁灭前朝,成为新一代的牧羊人——历史基本就在这种暴君和暴民的轮流坐庄中轮回。
回到“武侠”这个完全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
游走于庙堂和江湖边缘的“侠”,以一己之力行一己之正义,明显挑战了正统的权力秩序,与盛世嘉年华唱反调,可谓不被驯服的精英。如其暴力不能被赎买(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那他很可能就要被君主和已收编的精英们剿灭。《水浒传》的结局虽令人郁闷,却贴近该朝现实;而晚一些的清官侠义公案,却不过是文人冀望能安全和道德兼得地行侠的某种意淫;只有现代武侠才敢直言否定君权,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云中岳的《浊世情鸾》、萧逸的《无忧公主》等,侠以暴力而不合作,江湖规则基本上压倒了朝廷王法。特别是温瑞安的《逆水寒》,因叛逆之罪被朝廷追杀得走投无路的戚少商等群雄,反以胁迫皇帝重新下一道圣旨来纠案获得最终翻盘,将君主威权的荒谬性展露无遗:以前追杀你是对的,现在给你也平反还是对的,只有君主的伟光正永远不变,你根本无处说理。
个别如卧龙生的《剑气洞彻九重天》、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不耐烦的文人更指挥着他的侠客们挥剑直接割掉了无良皇帝的脑袋。
但如果梳理一下江湖叙事者笔下的各类江湖,为君王或强人唱赞美诗还是主流的。
梁羽生的天山系列里,他对清朝皇帝的厌恶固然从始至终,但其唐朝游侠系列中的武则天却光芒四射、君仪天下;金庸也是前倨后恭,乾隆被他写的人品猥琐,一钱不值,但乾隆的祖父康熙却被他夸得雄才伟略,鸟生鱼汤。
司马翎几部明朝历史背景的核心作品,侠客仗剑基本是为君王了却天下事。如《玉钩斜》最后一节,主人公无论在暴力上如何出神入化,其人生价值最终还得在“奸党方面可能不顾一切发动阴谋,东宫太子很危险。为了国家,我得赶快回去保护他。”
秋梦痕的《黄金客》中, 主人公古士奇自幼孤苦,历尽九死才练就盖世绝艺,但原本任其自生自灭的变态祖父、父母等长辈就大义凛然出来抢摘果实,告诫主人公反清复明才是人生正道,而原本倜傥不羁的主人公也即刻体会了家族的苦心,对一个狗屁不通的前明遗臣刘恨觉俯首听命,辅佐一个更不通的朱王孙,让人看得很是不爽。
就连桀骜不驯的古龙,在少有的几部提到皇帝的书中,对这个符号也是用语忠厚、不敢得罪的。如小李探花夸赞心树大师“一入翰苑,便简在帝心”;又如《陆小凤•决战前后》,不仅叶孤城要刺杀的皇帝,风度见识,无不卓然出尘,而原本翱翔九天的陆小凤第一次到了天子禁地,“也不禁觉得身子里的血在发热”。
黄易在《大唐双龙传》中也曾将主人公寇仲塑造成一个能与李世民相抗衡的绝世英雄,但“终不能违背历史的基本事实”,面对天命所归,寇仲最终只能主动让贤,抛却满腹雄心大志,成为圣君李世民治下的一介庶民。
……………………
书单还可以列的很长。
显然,在文人(或者说文学化)的江湖里,任你是如何杰出之士,失去为皇帝服务的信念都不足取了。如果今世你运气好遇到千世而一出的圣君,还惦记着替天行道以武犯禁,那你不是没头脑就是没良心。至于圣君本是千世而一出的常理,他们根本就视而不见。
此外,还有一种“侠”是彻底融入江湖的,只知江湖规矩而不知庙堂王法。这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终不舍圣主情结的,喜好让他笔下的人物一路向着江湖王者如武林盟主之类的宝座进军,在此途中,遇神弑神,遇鬼杀鬼。但一般而言写到笔下人物夺取江湖王座就截止了,毕竟盟主只负责生杀予夺和决定羊群往哪里跑,群豪得自己寻草吃;且阅读的高潮已过,也就没必要再关心怎样治理乱哄哄的群豪那些乏味的事了。
另一类则如王怡所言,是不会傻乎乎去为皇帝服务或者去论剑争天下第一的虚名的,他们都忙着抢地盘开分店,通俗一点讲就是得实惠。典型如古龙笔下的上官金虹和孙玉伯。
上官曾对小李探花慨叹“你本是三代探花,风流翰林,名第高华,天之骄子,又何苦偏偏要到这肮脏江湖中来做浪子”。他显然把庙堂和江湖区分得很开,对庙堂无敬意但也无敌意;而脱胎于“教父”的老伯,他的江湖里更完全只有黑帮规矩而无朝廷王法。
但回到他们威权的建立上,这两个枭雄也不外乎以收买和暴力来威慑江湖精英们为他**而已,骨子里还是强人兼寡头统治。老伯要稍胜一筹的是,上官纯粹是一台权力机器,他对下属的唯一要求就是绝对的服从。古龙不无讽刺地写道:他们(金钱帮人)都没有嘴,因为他们根本不说话,纵然说话,也都是上官金虹的声音。他们没有眼睛,因为他们根本不用看——他们能看得到,也全都是上官金虹要他们看的。他们只有一个很小的耳朵,因为他们只听得见上官金虹一个人的声音。而老伯在流亡途中曾对他以前的种种统治手段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认识到以往下属的服从并不等于对他决策的尊重和同意,有时仅是对“老伯”这个权力符号的盲从而已。
显然,作为权力者的老伯,他的自省也是靠不住的。直到《流星蝴蝶剑》的最后,我们也看不出老伯对他的权力运行机制采取了什么真正的改革措施。个别细节还显示,易潜龙帮他训练出来的新血,仍然视其为真理所寄的神或圣君。尽管古龙也曾在《三少爷的剑》中让谢晓峰道出“我想要每个人都自由自在的过他自己愿意过的日子”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话,但谢晓峰潜意识里自封君父和救世主的味道也很明显,尽管他并没有这样的权力欲。谢晓峰最终只能自削手指来遏制自身暴力,充分说明把梦想寄托在暴力者的自我阉割上是一件多么不靠谱的事。
曾经有一种圣贤的说法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其中包含的某种逻辑就是“有什么样的君王,就有什么样的精英和民众”。但实质上有什么样的民众,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君王。哲人在《乌合之众》中慨叹民众之不理性: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群雄因为缺乏天赋和正确的信息渠道,所以焦虑不安,而为避免自己作出错误选择的最简单办法就是诉诸无所不能而又宅心仁厚的圣君或者强人——因此群雄的行为逻辑才那么奇怪:他们可以敬畏东方不败而敬爱任盈盈,而完全无视这两人其实都是他们苦难的发源地;他们也可以因为乔峰身为一个契丹人而劝谏辽帝,就忏悔起自己误信“乔峰是契丹人”的过错,而无视契丹人中某个人如何就不能具备悲悯情怀的可笑逻辑。带头大哥们自然在心中窃喜,他只要稍稍顺势而为,他的威权就可无坚不摧。而最可悲的地方无疑是,群雄明明走的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却自以为走在朝圣的光辉旅途中。
滔滔江湖,永远不改的是强人称王。
在所有的江湖里,群雄的自治能力都是被深深怀疑的,他们永远需要一个代表“君父”的牧羊人角色。这一点毫无疑问也毫不奇怪,创作江湖的文人们身在这种文化格局的彀中,他笔下的群雄自然同样走在寻找圣君的永恒路上。
金庸似乎最后找到了:老人家用《鹿鼎记》来证明,一万个仁义之侠也比不上一个好皇帝。现实中他还曾荣任香港基本法立法委员(这在古代至少相当于太子洗马吧),实现了经天纬地为帝王师的文人最高梦想。而梁羽生江湖的苦恼就在这里,假如他笔下的义军真的推翻了万恶的清廷,群雄又得过怎样的日子呢?难道义军还能依法治国不成?即便真能,大侠们再携带管制刀具上街就是非法了,精英们都成了米粒之珠,光华不在,武侠的迷梦如何还能编织下去?
因此把文学中的侠视为正统权力秩序之外实现个别正义的某种补充手段,毫无疑问是一种理性;而能意识到这种符号还寄托着芸芸众生对发掘自身卡理斯玛特质的热烈向往,意识到被长期塑造为顺民的人们,总有种不可遏制地向威权证明他的思想并没有彻底妥协的冲动,这才是江湖真正令人感动的地方。就我看来,这正是武侠文学永恒的价值所在。
最后说说圣君的命运吧。
圣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指点群雄道: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决不会是你们!这大致是不错的,群雄虽以惊人的破坏力呼啸而过,一路留下狼烟和鲜血,但在历史上确实只能每每被冠以“乌合之众”之名,他们中的个体面貌一般都是模糊的。然而圣君对这种力量相当忌惮——既然君王这个符号意味着垄断一切利益,那他的梦想自然是希望这个权力格局永远维系下去,直至千秋万代。而如何钳制群雄,使其不敢、不能尤其是不愿造反,就是圣君们的头等大事。
大致说来,让民众休养生息、以圣贤之说进行教化、以铁血武力慑服群雄、收买精英以及发挥君主自身的卡里斯玛特质等均为有效的治国之道,古今中外一以贯之。但时至今日,这一套似乎都不太灵光了。比如北非的民众们甚至不需喊“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而君主们已然狼奔豕突,苦心经营多年的王朝瞬间成为昨日之黄花。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往往以圣君始以暴君或者独夫终,尽管圣君的后代自食其果、血脉无存,但中间往往还是有一段颇长的盛世嘉年华可追忆的,而如今的君主竟然有一世之危机,时代变化之快,令人长叹不已。我族被豢养的精英们还在迷惑被圣君频频赐以子女金帛、过的相当不错的群雄如何愿意把脑袋别在腰带上干这流血勾当?甚至不无腹诽地认为这些黑蛮子群雄不过又是一代乌合之众,胜利果实迟早要为新一代的牧羊人摘取之时,那边的游牧圣君终是要不可阻挡地陨落了。被圣君塑造过的群雄既然有决心、有行动让他们的下一代不再被塑造,那么迎来的自然是一个全新的江湖。在这过程中所经历的炼狱之门,那题词始终在那里镌刻着呢: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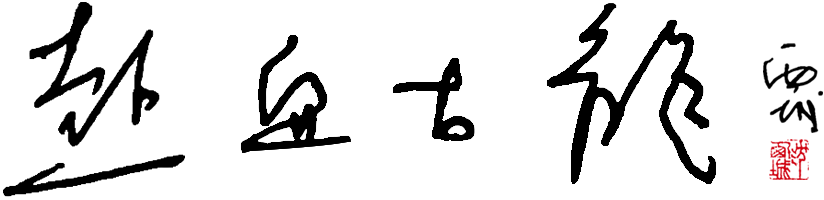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