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客户端,2016年7月27日
凤凰文化讯(冯婧香港报道)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来说,“武侠”的复归可以说是一大事件。1981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金庸,武侠文艺开始成为流行文化中最为缤纷多彩的风景。80年代末到90年代,所谓“华人武侠四大天王”开始风行,这一称谓可以说是囊括了当时的老中青三代:同样出生于1924年的梁羽生和金庸可以称得上华人当代新派武侠的开山鼻祖;出生于1938年,于1985年就英年早逝的古龙是中生代武侠作家中最为闪亮的明星;出生于1954年的温瑞安则因其独树一格的诗化武侠作风与前三位大师并驾齐驱。
在几乎同时接受“四大天王”的中国大陆,温瑞安得天独厚地获得了广泛的人气。八、九十年代的大陆武侠文化通过两种媒介得以传播,一是电影、电视剧,二是“租书摊”。随着香港影视剧的陆续传入,几位长期提供电视剧脚本创作的武侠作家反而比纯粹的武侠作者更让人耳熟能详,这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打造了“四大名捕”优质形象的温瑞安。在“租书摊”方面,在梁羽生和金庸封笔、古龙逝世之后,温瑞安近乎动物凶猛的笔耕不辍使得他构成了唯一一个能让大陆读者期待“连载”的优秀武侠作家。
相比起金庸的凝重与豪迈,相比起古龙的跳脱与悬疑,温瑞安的作品系统可以说融合了两人的特长,又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诗化”风格,从节奏鲜明、气势磅礴的“四大名铺”系列到带有自传色彩的“神州奇侠”系列,再到超凡脱俗的“说英雄谁是英雄”,温瑞安把武侠带到了新的境界,开辟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流派。
2016年7月24日,第27届香港书展上,这位传奇巨侠击鼓而歌,以一曲铿锵的《将军令》作为“此情可待成追击——我们早已‘复仇者联盟’”主题讲座的开场白。
现场的观众不解其意,何谓“复仇者联盟”?又要向谁“追击”?
毕竟,在许多老牌武侠迷的眼中,武侠小说最风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大师也已经远去,在这个时代谈论“武侠”和“武侠精神”,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最鼎盛时,台湾和香港有超过七百人在写武侠,而现在的年轻人早已抛弃了武侠小说,他们的案头书大多都是剑侠玄幻、宫廷穿越,或者是历史传奇。
但温瑞安认为,武侠小说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样日薄西山,而恰恰是处于方兴未艾的最好年代。武侠小说正在经历一场异化,在信息时代呈现出诸多形状,像异形一样,进入人体内慢慢酝酿、埋伏,然后异化、取代原有的地球人。武侠小说不是行尸走肉,可是它的每一次灭绝都是重生。他从本土和西方的两个层面来论证,武侠是如何不断异化并重获新生的。
在他看来,当下流行的剑侠、玄幻、宫廷、历史类小说,都是武侠小说的遍地风流的分支,也是最新的载体。武侠小说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所谓的“正统”也并不存在,如果以平江不肖生为标准,可能金庸也并不正宗,可是他集各家之大成达到武侠的巅峰,把武侠小说推进文学的殿堂,当之无愧地是空前所无的武侠大师。
“当年还珠楼主写《蜀山剑侠传》的时候,穿越、仙剑,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可是整体上表现的还是武侠小说的格局。当时南北二家双峰对峙,平江不肖生写《近代侠义英雄传》,把戊戌六君子的历史融会贯通进去,也是武侠小说,后面《江湖奇侠传》里高手闯出刚家的门户,就是日后的通关游戏。剑仙是我们影响的,奇幻是我们分支出去的,这些游戏就是我们慢慢变成鬼魅化的,《惊风剑影录》和《大内群英传》就是宫廷,琼瑶阿姨写还珠格格也有武侠小说的体现。”
温瑞安还指出,很多西方特别是好莱坞的鸿篇巨制,都受到了中国武侠元素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你看《复仇者联盟》和《分歧者》吗,《分歧者》中人类被分为五大派系(无畏派、博学派、诚实派、无私派和友好派),就是我们武侠小说里面的五派掌门,这些都是金庸先生搞出来的,可是在美国好莱坞市场他把它推动了,在国内包括在香港也能卖。《X战警》更是如此,《黑客帝国》的枪战是袁和平导演的,密室交手用的就是咏春,那个女人从建筑物出来时完全是武侠的形象。而这些内容,徐克的《黄飞鸿》里早就有了。
于是开篇令读者费解的命题也呼之欲出了。“现在西方特别是好莱坞,把我们武侠里头所有精彩的桥段、把我们的武侠精神和表现形式都抄去了,所以我们要搞一个‘复仇者联盟’,把我们中国这些派别,这些武功都拉回去,你抄了我们的,我们来复仇。”
为什么人家拍的那么好,令人如痴如醉。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追击”和“复仇”呢?温瑞安说,过去我们的武侠电影在包装上缺乏逻辑性,无法唤起大家共情,但西方的经验表明,武侠一定要现代化,而且也是可以现代化的,武侠要“借尸还魂”,不能永远只用金庸和梁羽生的路子。除此之外,也要注重保持我们武侠的民族特色,只有这样才能拍出真正“现代”的武侠电影。“不要忘了我们中国电影最开始受到关注,是台湾胡金铨导演的《侠女》和《龙门客栈》,是金燕子和大刺客,就是因为它们都有一种民族的色彩。”
温瑞安强调,在这个IP时代,我们要趁机组成“复仇者联盟”,建立自己的庞大产业,去“收复失地”。他还“利诱”现场的年轻人去积极投身武侠电影产业,“光是IP版税、影视,我这半年来收到的版税大概没有少于四千万。”他还透露,截至目前,他对自己作品改编的28部电影统统不满意,这可能是信息化时代的阴影部分,创作者的心血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是被过度消费了。但他豪情万丈地说,自己的传媒公司正在积极投拍武侠电影。同时他也表示,自己的第一身份永远是作者而非商业,最让自己骄傲的也是忠实而庞大的读者群,而非巨额的版税。
如果“侠”不能够发生在现代,那就是无缘的回声,它的存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有鉴于此,当今社会的侠义精神如何自我言说,就变成了一个更为核心的命题。
在温瑞安看来,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好的警察来维护正义,需要好的记者去大胆披露,也需要好的作者去忠实记录这个时代,需要好的律师可以不要钱地为弱势群体做申辩。金庸提出来的侠之大而者为国为民了不起,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为国为民。古人云齐家平天下,但现在的天下不是想平就平的了的,“你现在去为国为民可能第一个就像我一样不见了好多年”。在当下,温瑞安提出了另外两种表现形式,同样也是侠者精神的彰显:侠之中者为情为义,侠之小者为友为邻,我们尽可能去另外帮一下旁边的女同志,或者在街边的窗边点燃一只灯。
具体到自己的侠道,温瑞安提了两点:一个是不欠情不欠义,所以不管有多少红粉知己,最爱的都是风雨同舟的老婆;另一个则是多记恩义少记仇,所以回忆起当年被所谓的兄弟出卖的经历时,他一笑置之。
这种侠道也是温瑞安与生俱来的豪侠情结和诗人气质的集中体现。1972年,一群共同在马来西亚创办诗社的年轻人,在中秋节的夜晚醉酒狂歌,他们“笑着闹着哭着”。18岁的少年温瑞安目睹此景心有所感,记下了那天圆圆的月亮,和月亮下谈心的人们。如今,一同读诗唱歌的的好兄弟早已风流云散、各自天涯,“但没关系,我想念他们”。幸好诗歌是超越的永恒的存在,在世事巨变后的今天,他还是可以唱起《将军令》,还是可以朗诵《月光会》,“直到那坐着的人忽然变成了一堆白骨”。
月光会
——致时间
那坐着的人忽然变成了一堆白骨。
不久以前我们曾在那边的那边开过月光会
那时候人很多又很齐大家笑着闹着哭着
直到很夜很夜的时候大家都睡了除我
我呆呆望着那两盏最后焚毁的灯笼
今年月光会人也不少也非常热闹
但已少了两位生死同心的兄弟
我们围在圆圆的月亮下谈心
我们谈文学谈艺术谈写诗
每一个人的笑声与步姿
都深深地烙刻在梦里
夜深时大家都静默
互相地深深视着
感觉月之疾落
时间之消逝
残烛将尽
皆无言
无声
静
直到那坐着的人忽然变成了一堆白骨。
稿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费时三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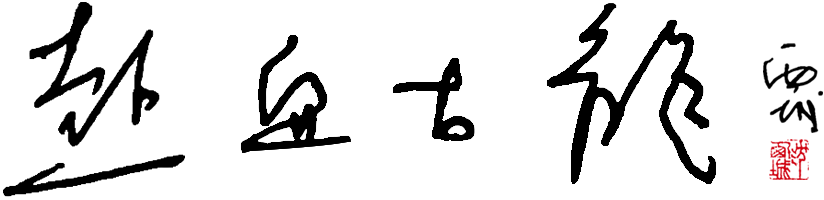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