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瑞安
余光中走了。
因为忙,我只好用简的文笔纪述、书写。
我大概在小学就看余光中先生的作品,到了初中一,开始迷得如痴如醉。大家都知道诗人余光中,但是我更爱他的散文,他的现代派纯散文,讲究节奏、意象、象征、音韵,中国文字在他手里,就像一个大型交响乐协奏曲,能各自为政,又能融合无间,不管是来一段甜美小曲独奏,还是明快悠美的圆舞曲,还是独奏一段管弦咏叹,或千弦万韵的大合奏,都长短火俱发,无一不精,无一不准,无一不美,无一不令人赞叹不已,吟咏不绝。当大家还在看余光中的诗的时候,我已经引导我“绿洲社”和十大分社的社友们,正在谱唱余光中先生的诗为曲子,又手抄书写他的文章诗文,广为流传,在我们的手抄本上刊出。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用手抄?1965~1968年的时候,我们那儿连影印也办不到,但我们愿意手抄,抄一首(诗)背一首,腾一篇(散文)记诵一篇。台湾两位感情至深至挚的人,如今都已不在人间了。
当时我还在大马,16岁,写了龙哭千里,大江依然东去,迷神引,魚龍舞,向风望海,八阵图等过万字的纯散文,后因高信疆先生而发表在当时台湾知识分子第一大报“中国时报”刊出,算是非常触目,以致后来我在台湾大学初入学一年班之时,居然天天都有学长学姐还“慕名”前来找我这个来自大马的华侨小愣头签名结交的。
当时,(1971年左右,也就是大约是我开笔写四大名捕前兩部的时期)我的诗作例如:佩刀的人,碑帖,袈裟,惘然外记,刀和月光会,水龙吟等诗作,因信疆先生引介,让余光中先生看到了,他大力推荐到并发表于台湾当时权威性和学术性的文学刊物:中外文学,现代文学,纯文学,蓝星诗刊,中华文艺等月刊及期刊,均在重點推荐及发布。这都是我的荣幸。
到了73年,我在大马考取了台大学位,赴台之前,须办签证,余光中那时已是美国爱荷华大学回到国内,从旁知道我正在申办,马上写了一封推荐函给大马领事寫,内容大概推介我是個才气纵横,品学兼优的傢伙,应为台湾文化当局列为力争对象。
由于余教授当时向我约稿,他的字寫得鉄划银钩,比印刷出来的字还要端正显眼,而且信封上总是瑞荘明丽的写着:“温瑞安学兄大启”。我甚为汗颜,又极为感动,而且感激当时台湾,因为政治上的压迫感与自卑感并发症,对东南亚过去的旅客,非常严防,每过境海关,均遭“翻箱倒箧”式的检查。我第一次(19歲)赴台,当然也不会遭遇寬容,我的皮箧子和旅行袋,几乎给毁容式的翻查,他们见书撕书,见公文袋拆公文袋,直至他们找到了一封信,上面印着“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你信箋,上面手书:“温瑞安先生大鉴”,下款“弟余光中谨呈”,那海关官员遂脸色一变,骇然问:“余老师是你的什么人!?”
1973年,我受邀出席台湾圆山大饭店召开的“国际诗人大会”。当时余光中先生演讲,我也去了。记得余先生在文章曾写过,他在美国聆听他心仪的诗人演讲后,很想偷撷他一根白发在手心里珍藏着。我听我心爱的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我连他的小说《食花的怪客》,也在40多年前都读了)演讲,也想偷拾他一条银发珍藏于怀。現在,我亦已白髮蒼蒼矣。什麼花甲少年,仍舊歲月驚心。没想到,演讲完毕,他还特别“嚴选”我和几位兄弟朋友,由信疆先生陪同下,在余老师寓邸,论诗论道,通宵达旦谈文学。在天破晓时,我们这群为中国文化反復討論要找一条出路的知识份子,看到夜未央前天灰濛濛、深秋初冬,寒意凛人,信疆长叹一口气,对我们说:“现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处境,真是月落乌啼霜满天啊。”我和我的结拜兄弟清啸听了,热泪盈眶、欲泣懷憂。
迄此以后,我办“青年中国杂志”、我创“试剑山庄”,我编“神州文集”,我开“刚击柔至道”武馆,我办“神州社”……全都为了尽一己之力,为中国文化和文学、乃至侠义文化、侠情精神去寻觅一条出路、一條活路、培養一些人材,言軽人微位卑,但始終不敢忘國。生许或不能有所成,但尽我所能、舍我其谁。
有一段时期,大概是77-78年期间吧,余光中给一群打着“本土旗号”的作家们(有不少还是他大力培植成名的)在文坛上「展開圍剿」,冠予他各种不同的帽子与罪名,这些所谓本土作家们(我看他们对台湾本土也不算关心更不了解)对他口诛笔伐,不忍卒覩,这些人想联络及说动我及我们的神州诗社也加盟围攻余师,我唯一应对的方法是:跟他们一概都绝交了。
我在台期间,我也极少去拜会或骚扰余老师。我很清楚知道,艺术工作者,特别是作家,是需要自己的时间,也应该保持一定的寂寞的。
可是,不久之后,我的神州社在台湾,就给无辜承受浩劫了。之后又数年,我辗转流亡,几度到香港暂居,而且允准居留之两周,使给逐走。那是因1981年,正好余光中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余光中先生有四个女儿,珊珊、幼珊、季珊、佩珊,知书识礼,又有才华,长得漂亮,都曾加盟我神州诗社,而且表现优秀,受我赏识重用。余家四位千金,对我很敬重、服从,社友们对她们也很有好感。我在香港留之期间,有次余光中先生在艺术中心办诗歌朗诵会,我挤身观众群里,没想到给季珊发现了,她在余光中老师上台公开朗诵之前,趋近跟余师说了:“温大哥也在现场”。
密密麻麻的观众期待他开腔,于是,余光中先生在朗诵前说:「今天晚上,我们来了一位很特殊的,有才华的贵宾,他就是温瑞安先生,他也是位优秀诗人,才华独一无二,而且还是位青年武侠家,并有领导组织能力,可是给台湾政治单位误会了,使他离开台湾,暂时寄居香港,他今晚也在现场,让我們用掌聲歡迎他。」
大家听了,掌声响了起来。我那时“流亡”已一年多了,四海为家,无可归,四处流浪,无人要。前进无路,退无死所,在港也不能久留,对外不能露脸,连在中港台出书发表,也不能用真名实姓,余师这样公开一提,群众在灯光火亮中,掌声足足响了三分钟,还有人在群众中大声吆喝:“温瑞安,你好嘢!”
我真是哭了。
泪崩的跟狗一样。
过了两个多月,清秀杂志老总蒋芸小姐“收留了我”。她本身也是台湾文坛的名人,也是美人,而且也是名编辑(据说大学问家才子李敖也曾追求过她),她跟余光中先生熟悉,亲载我去青山寺拜神许愿之后,再帮我和方娥真去中文大学教授宿舍去拜会余光中伉俪。那一次也是相谈甚欢,余师对我温厚亲切,余氏姊妹待我一如既往,视我为兄长,可是,余师母忽然肃容说:“余老师平时又要教学,又要研究,而且要参加学术交流会议,非常忙碌,你没有事就不要来打扰余老师,更不要打扰我的家庭。”
我听了。
我明白。
在台湾发生的诬陷,也许,并不曾影响余老师,余家姊妹也或许仍然相信眼前的“温大哥”,但却不是人人如是。也许,余师母或者他人也不知晓,我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人。否则,我在45岁前就写了二千万字的作品是怎么来的?是我一个人在书桌前一个字一个字炼出来的,书也是一本一本写出来的。是的,我有过逾一千多位结拜弟妹,办过超过二十个有组织的公司、文化、武馆、娱乐公司,但那都是我应世随俗不得已的对应之策。我本身不喜欢打扰人,可以不应酬、不饭局、不烟不酒,逾40年之久,人家交朋友是交一个多一个,我是好友去一位少一位,到近年交友精选尤慎,不但自己几乎绝少致电予人,而且也不接电话,电脑也不用上。光是今天来了位身份非凡的贵宾過來會我,原则上要合作应予一见,但我因为乍闻余师走了的噩耗,还是回避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是寂寞,我好寂寞,我甚至爱上寂寞。是的,我喜欢朋友,我好交友,但我愛寂寞尤甚。当时,余师母既是这样说了,我也不解释多一字,一晃眼,已36年矣。今天乍闻,余师走了……像余光中这种绝世人物,绝世才华,绝世才学,不是每个时代都可以有,每个人都可以企及,每个地方都可以出现。“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我非狡兔,却营四窟。我曾说自己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余师是四项全能。但我最服膺他的是:对中国深沉久远的爱,对中国文学久远深泺的爱,还有对同济及后辈的栽培与爱护,如今,有谁能有他那温文儒雅,博大精深而且兼得雄伟秀美的文体兼举?余师已逝,谁来看惊涛裂岸,听听那冷雨,卷起重楼飞雪?光中已黯,现代诗谁有古典风华,传统余韵,谁敢轻言:我要对付的不只是一只老鼠,而是整个黑夜?莲的联想,望乡的牧神、吃花的怪客、焚了琴、煮了鹤,他仍在光中,而我卻仍然是京华尘里客,独来绝塞看月明!
温瑞安
2017/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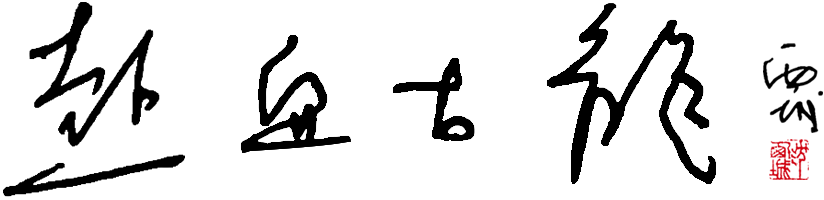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