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中
《香港联合报》的大楼座落在土瓜湾的海边上,孤零零的,纪录著一段历史。九零年代初,两大台湾报业集团相继登陆香港,建立桥头堡,目标瞄准中国大陆市场,一报一刊(《香港联合报》和《中时周刊》)曾经喧腾一时,给香港带来了另一种文化。《联合报》还在香港投下钜资,买地皮,建大厦,做长期作战的计划,气势逼人。九五年大厦建成了,刚启用不久,报纸就突告结业。在此之前,《中时周刊》也已停刊。只不过短短几年功夫,台湾传媒从香港全面撤退,终结了他们的”大陆梦”。
《香港联合报》编辑部近万呎的旧址空荡荡的,只有薛兴国和我,背景是靠墙排列的几千张CD和音响。薛兴国玩笑地说,他把家都搬来了。在香港,薛兴国可称是传媒前辈。他是香港人,六七年入读台湾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后留在台湾,加入联合报系集团,先后出任联经出版社副总编辑、《新生报》总编辑、《香港联合报》副社长等要职,现任联合报系集团香港新闻中心主任。他最有趣的人生经历之一,是与古龙结为莫逆之交,是古龙最后十年肝胆相照的死党。早年他写过武侠小说,常给古龙代笔,最近还改写了王度卢的《卧虎藏龙》,在台湾出版。
给西方人看的“天桥把式”
张文中:大概从来没有一届奥斯卡金像奖,像这一届如此牵动全世界华人的关注。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获得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十项提名,空前大热,虽然到最后只得到最佳外语片等四个奖项,令不少人失望,但毕竟是华人电影进入西方主流电影市场的一个很大的突破,甚至有人预言这将带动整个华人电影进一步走向全世界。不过,从去年电影上映之后,你好像一直持有一种批评的立场,认为这是一部完全拍给西方人看的电影,你的理由是什么?
薛兴国:我的根据,第一,是这出电影的爱情观。李慕白在临死之前突然冒出一句:我是深深爱著你的!这种爱情表白的方式,在中国传统的感情世界里是没有的,完全是西方化的东西。还有玉娇龙和罗小虎,两个人的感情就更露了,从两人打斗,一下子跳到拥抱一起,接著性爱缠绵,都出来了,这些根本不是中国武侠世界里的那种感情,而是西方式的感情。第二,电影的配音,一个广东话版本,一个普通话版本。周润发和杨紫琼是讲广东话的,在普通话版本里,台词说得就像小学生念课文,平铺直叙,表达不出他们的感情。另外两个演员,章子怡和张震是讲普通话的,又给他们配一个广东话版本。在中国观众看来,感觉上非常不伦不类,但是西方观众不是听配音,而是看英文字幕的,没有这个问题,等于是在阅读你的电影,让他们有想像力的发挥,你的演技能不能念出你的感觉并不重要,只要让他看懂就可以了。还有,几场武打的场面,俞秀莲本来是练双刀的,可是在跟玉娇龙对打时,什么武器都拿出来了,完全是给西方人看的”天桥把式”,中国武器怎么打,统统搬给你们看,看的是热闹。玉娇龙坐在茶楼那一段也是,跟许多人对打,那些人还各有不同绰号,中国观众看了很可笑,可是西方人会觉得很新奇,他们没见过的。
张文中:不过,这出电影传递的毕竟还是中国文化的讯息,因为武侠这个东西是西方世界里没有的,中国的武侠文化跟美国西部的”牛仔文化”也是不一样的。你不觉得这出电影也给西方观众送去了一种中国文化精神的表达吗?
薛兴国:即使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也是失败的。比如,电影里说到一种”宽恕之道”,玉娇龙偷了俞秀莲的宝剑,又杀了人,李慕白他们一开始原谅她,希望把她引到正路上去,对白里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影像里没有,根本感觉不到这种”宽恕之道”。李慕白又有一点所谓”禅学之道”,打起来好像很潇洒,但是在影像里也没有表达出道家的那种境界,只是看热闹。而影片的主要情节是爱情,这种爱情的表达又是西方式的。整个电影并没有表达出一种中国武侠文化的精神。很多观众对电影里的特技很喜欢,其实里面有许多胡金铨的影子,比如玉娇龙在酒楼打斗那一段,有人看完之后说,咦,这不是“迎风阁风波”吗?几十年前就拍过了。像竹林打斗那一段,就是靠起重机的怪手吊得很高,而胡金铨《侠女》也有竹林一场戏,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机器,可是他拍侠女从天而降,劈开竹林从中间飞过去,那种感觉好极了,你觉得胡金铨会输给李安吗?而且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不仅有一种“禅”的味道,而且整个都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连配乐都是湖南梆子。《藏龙卧虎》用的是马友友的大提琴,完全是西方的调子。
中国武侠文化精神
张文中:中国武侠文化的表达,最早可以上溯到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后来到唐人传奇里,到达一个高潮。到清末民初是又一个高潮,出现了平江不肖生,以及后来的还珠楼主和王度卢等等,不过他们笔下的武侠文化,跟史迁与唐传奇已经有很大不同。到了六十年代香港和台湾两地先后兴起新派武侠小说热潮,金庸、古龙、梁羽生又跟平江不肖生等有许多不同。你也写过武侠小说,不久前还用现代小说的写作技巧改写了王度卢的《卧虎藏龙》。你说的中国武侠文化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薛兴国:武侠小说,不管新派还是旧派,统统都有“侠义”的情怀在里面。在清末民初的各派武侠小说里,王度卢是以写爱情见长的。《卧虎藏龙》是一个系列,共有四部,从李慕白的师传,写到李慕白俞秀莲,带出玉娇龙和罗小虎,有了一夜情,玉娇龙怀了一个小孩,再讲二十年以后,罗小虎结了婚,他们下一代的恩怨情仇。王度卢最为人赞赏的,就是写情,他从“情”里演化出“侠义精神”。台湾的联经出版社得知李安拍电影,就要我把原著浓缩成一个中篇。电影开拍时,他们的剧本是高度保密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拍,于是我选了四部曲中的两本,从宝剑钦差开始,把李慕白俞秀莲和玉娇龙罗小虎四个人的故事纠缠在一起,用跳接的方式去写,写四个人在情与义之间的抉择和挣扎。当年王度卢想不出一个办法解决他们在情义之间的难题,现在我帮他想出来了。我认为在“情”里已经包含著“义”,关键是怎么样看破这个“义”,要走出这个心结。我让俞秀莲跟碧眼狐狸打斗时,为救李慕白她中了暗器,瘫痪了,李慕白带著她去疗伤,在整个过程中他的心灵发生了改变。不过写到爱情时,我还是比较含蓄的,保留了王度卢的风格。中国传统里对于爱情的表达还是比较含蓄的,连古龙那么新派的,也没有写什么“我爱你”之类的,像现在电影里那种台词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张文中:或许,这是因应市场的一种手段?不说西方人,就是现代中国人在表达爱情时也不会像古代那么含蓄了,电影不过是迎合市场和观众的口味,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感受,对它的要求也许不能那么苛刻。听说在香港的电影圈已经拍完,或正在开拍,或将要开拍的古装武侠片,加起来大概有三十部之多。电影市道这么差,会不会藉此掀起一个武侠片的热潮?
薛兴国:在香港,观众里有两种看法。一种是非常喜欢,另一种是非常不喜欢,都很极端。我相信,喜欢这出电影的观众,一定是受西方影响较大、看西方电影较多的。如果是从中国古代文学一路看下来的,你就会觉得电影很好笑,哎呀,怎么会拍成这个样子!文化差异就在这里。现在电影拿到奥斯卡金像奖了,在西方市场成功了,又有许多人开始跟风,这就像当年楚原拍古龙的《流星蝴蝶剑》获得成功后一样。当年的”武侠片热”,后来很快就拍滥了,没有人再要看了。而且,以前功夫片很多,是因为有一个录影带的市场。投资拍了很多功夫片,其实都进不了电影院,根本没有市场,可是卖录影带可以赚钱,因为海外有需求,包括黑人,还有那些墨西哥人都很喜欢看。至于这一波会不会也带动那个市场呢?不知道。其实,《卧虎藏龙》如果没有在竹林上那种飘逸的打法,还有拍北京城,利用动画拍出轻功的特技,或许不会那么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因为看那两场戏才去的,其他没有什么新奇。这出电影在香港和台湾的票房都不是太好,只是美国好而已。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营造出一个武侠片的气氛来,起码在香港感觉不到,我不认为《卧虎藏龙》会掀起另一轮的武侠片热潮。你看徐克的《蜀山》拍完了到现在还没有拿出来,就是对这个市场没有把握。
新派武侠小说的背景
张文中:其实从武侠小说本身来看,也早已没落多年了。所谓新派武侠小说的三大家,金庸写文化,古龙写人性,梁羽生写爱国,各有自己特色。而金庸、梁羽生都有报人背景,古龙的小说后来也主要靠报纸连载,这种武侠小说的热潮,跟报纸连载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薛兴国: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它当时受到读者欢迎,可能是因为除了报纸之外,没有别的什么文化消费渠道。六七年之前我在香港,那时报纸之外,只有电台,收音机当时也不多,而且电台不像现在二十四小时播音的,电视是六七年才出现的,那么长夜漫漫,怎么打发时间呢?武侠小说情节比较吸引,每天追著看报纸连载,好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而且,当时有一种爱国情怀,战乱刚刚结束,逃到香港来的不能回去,大陆当时被称为”竹幕”,一水隔著两地,香港和台湾的读者都借著这种小说,投射了这种情怀。六七年,我到台湾去读大学,当时台湾的武侠小说已经很成气候。它有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因为那时在台湾写现代题材的小说,国民党控制很严,除非你写反共小说。郭衣洞(柏杨)的那几部都禁了,还有一些文字狱,所以只有写古代的比较安全,逃到武侠的世界去,在那里找到精神寄托。那时,甚至连金庸的武侠小说也不准进入台湾,是禁书,他被视为左派背景。在台湾最早写武侠小说的,都是一些老兵,以前念过一点书,比较出名的有诸葛青云、卧龙生、独孤红、柳残阳等等,古龙出来的比较晚一点。这些所谓新派武侠小说跟旧派不同的,是写私人恩怨比较多,把私人恩怨带到一个大环境里,有些甚至连历史背景也没有了。当然,金庸和梁羽生除外,我认为金庸和梁羽生是介乎新旧派之间的人物。后来的武侠小说都不写历史背景,只写练功复仇什么的。我记得是柳残阳先有一点变化,他的《如来神掌》有一点神怪的东西。有人写得比较血淋淋的,有暴力倾向。还有写得很色情的,点了你的穴道,绑在柱子上,做一些苟且之事。不过,一般而言,色情比较少,因为台湾公开还是禁的,色情一类的只能在地下流传,在租书店里看到。台湾新派武侠小说的流行,跟租书店的普及有很大关系,当时台北市每个区都有好几家。学生跑到那里,登记身份证,交一点押金,花很少钱就可以租回去看,流通很快。古龙的书,早期主要是靠租书店而写起来的。当时出书,都是薄薄一本一本的,一百多页,八万字左右。古龙写了一本之后,去拿钱,然后叫朋友喝酒去,喝完了再写一本。
古龙人生另一面
张文中:你当年也写过武侠小说,跟古龙是知交,一起喝酒喝得很厉害,还听说当年古龙来不及写的时候,常常由你代笔?
薛兴国:其实,我写得并不多,只写了一部而已。用的笔名司马雪,还是古龙给我起的。朋友说我写得多,哈哈,是因为我给古龙”擦屁股”擦得多!那时我代他写了不少。很多古龙小说里有我写的段落,这里一段,那里一段,他喝醉了酒,一个礼拜不动笔,我就帮他补一个礼拜,他酒醒了,由他继续写下去,接著他又醉了,我再给他补。像《陆小凤之凤舞九天》,他写了开头八千字,说我不写了,兴国你帮我写下去!古龙在这本小说的开头创造了一个天下无敌、无人能杀的人,你叫陆小凤怎么去杀他?不过,小说的卖点也在这里。后来,我把这个人写得很”色”,一看到女人脱光衣服会定一定神,就在那一瞬间,陆小凤出手把他杀了。朋友看了,说这个很刺激呀,古龙也说好,而且这个情节在电影里能卖座!这是我给他创造的。改编成电影以后,有人还对我说,这个著作权费应该你拿才对,我说,哎呀,算啦!拿什么呀!早期给古龙代写的,有很多人。他有什么事来不及写,常常找人帮忙,给他收一收呀。特别到后期他写报纸连载,常常喝醉,第二天报纸等著登出来,就没有办法了,一定要找人代写。所以,后来报纸约他写连载时,先要来问我,万一古龙喝醉了,找不到他了,你愿不愿意帮他写?不过,古龙最好的小说都是他自己写的。小李飞刀从头到尾全部是他自己写的,没有任何人代他写。当时,主要是两家大报连载,《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每天一个栏,一千两百字左右,一天两千多,对古龙来说,写起来其实很容易,因为他最擅长写短句:是。是吗?真是。真的是吗?就是四行了。报纸是以行数来给他计算稿费的,你不能给他计字数的,而是计行数。到后来古龙红了以后,有点想写哲学的东西,于是写了《天涯明月刀》,在《中国时报》连载。余纪忠看了之后,可能觉得在武侠小说里谈人生谈哲学,节奏太慢了,很不满意,下令停了他这本小说的连载,所以这本小说最后没有写完。古龙很不高兴,后来他的武侠都在《联合报》连载,再不给《中国时报》写了。
张文中:古龙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武侠小说?
薛兴国:总共写了一百多本吧?七十年代他写武侠小说开始有了名气,他小说的悬疑性被大家注意到,到八十年代他的小说大量被改编成电影,就非常红了。他的小说,光卖旧作的著作权就很可观。我记得有一年他收了七千多万台币的著作权费,很可观呀!可是几年就被他花光了。他跟老婆离婚,我想他老婆带走一笔钱吧?他自己也很会花,喝酒,XO,搞女人也搞得很厉害,太风流了,每天没有女人不行,也因为那些小明星看他红了,想在他的电影里轧一脚,那时他的身边真是美女如云。他买了一辆最新式的跑车,后车盖一打开是整箱整箱的XO。那时台北流行XO,走私进口,两千七百块台币一瓶。他都喝XO的,每天晚上请朋友吃饭,如果是十二个人,就有十二瓶XO在桌上,每人喝完一瓶,就是三万多块。这是一顿饭。台湾吃饭跟香港不一样,从六点钟开始,吃到九点钟一定散席了。然后是第二摊,酒廊或酒家,到十二点。接著,再去北投,找酒女陪,喝歌,有点像卡拉OK,不过有现场乐队的伴奏,再玩到半夜。天天跟他跑几个地方,那时我酒量很好。古龙去世时只有四十七岁,因为喝酒喝得太多了。给古龙举行葬礼时,王羽说他要送四十七瓶XO给古龙陪葬,后来大家一想,不行,XO很贵,一算差不多十多万,怕人家盗墓,最后决定在古龙葬礼上喝掉,于是大家就在他的遗体旁边,把整整四十七瓶XO全都喝完了!
张文中:你跟古龙这么熟,你觉得古龙是怎么一个人?
薛兴国:我跟古龙交朋友,认识的第一天,就睡在他家里,他大概觉得我对他没有戒心,就把我当成了朋友。后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对我特别好?他说,就是因为你那天在我家吃饭喝醉了,然后睡到第二天才走!那时他还没有红,他的小说后来拍成电影才大红大紫起来。古龙小时候的事,没有人知道。他自己说是从香港过去的,到台湾念高中,之后考上淡水英文专科学校,不过可能没有毕业。他外文不错,一直喜欢看西方小说和日本的推理小说,在学生时代开始写武侠小说赚稿费,就这么混生活。早期的《大秦英烈传》,看起来有点闷,不像后来写得那么流畅,因为在开始时他是跟著诸葛青云、卧龙生那么写,和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到后来他从日本推理小说和西方《教父》那类黑社会枪战小说里找到自己一条路,摆脱那种“练功复仇”的模式,形成自己的写法。古龙很喜欢日本的推理小说,一个是那种悬疑的技术,另一个是人性的描绘。他说过他很喜欢松本清张,你看松本清张把一个社会融入一个推理故事里,一件谋杀案带出来的是一个社会的种种问题,古龙就很想走这条路。他也喜欢美国的黑社会小说,像《流星蝴蝶剑》,有人当面问他,他说他在学《教父》。古龙是很想创新的,他创造了像楚留香这样一个侠客,风流潇洒,专以偷为生,但是不偷穷人,只偷有钱人,非常好玩,又非常讲侠义。还有《七种武器》,他就很想写“恐怖的武侠”、“幽默的武侠”等等,把七种武器都融化在里面,可是写完《血鹦鹉》之后,《一口箱子》写到一半,他就去世了。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比如他写李寻欢,《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小李飞刀,古龙小说里最有名的一个悲剧人物,性情非常忧郁,这样一个人物是在他新婚燕尔时写出来的。可是,在他失恋时,穷愁潦倒,却写了一本小说,叫《欢乐英雄》。在他最快乐时,他会想到他的忧郁;他很忧郁的时候,却创造了一个欢乐英雄。他在创作时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你说他写人性写得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在快乐的时候,他有一种不可靠的预感,觉得快乐是暂时的,心里想的是忧郁。
张文中:古龙的人生经历里,也许隐藏著一些不为人知的悲剧,在小说里他总是说到最好的朋友也许就是你最大的敌人,大概也是他人生经验的流露?
薛兴国:对,还有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都用滥了!古龙经历的人生波折很多,小时候他父亲为了一个女人离开家庭,走了,他们几个兄弟姐妹流落社会,后来他自己写武侠小说为生,他妹妹做什么我不太清楚,可能做过舞女等等,母亲的事他从来不对我们说,总之在喝酒时他从来不提自己悲伤的事,只谈他如何豪放如何开心。古龙就是这样的人,他总是把欢乐带给别人,把悲伤埋在心底。到了他写武侠出名,失去联络多年的父亲患柏金逊症住在医院里,提出想见他最后一面,他挣扎了很久,不愿意去。很多朋友劝他,还是去见一见吧,但是那时古龙太红了,很有钱,古龙怀疑他父亲当年抛弃家庭找的另外一个女人是不是想要谋他的财产,到后来他终于熬不住了,毕竟是父亲,我们几个陪他去医院看望他爸爸一次。在他的武侠小说里,其实投射了他许多个人的经验。
“武侠热”风光不再
张文中:新派武侠小说到八十年代到达高峰,到九十年代突然没落下来,在香港和台湾两地都是如此,这是什么原因?
薛兴国:武侠小说在十年前开始没落,有许多原因。一个,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图像化,现代人已经受不了文字的慢吞吞,所以不仅武侠小说,而且整个连载小说都在报纸上消失了。还有一个,是许多武侠小说作家到外国移民了,这些人也好像江郎才尽,已经写不下去了,不像古龙那样一直会吸收新的东西。同时,即使古龙本人,写最后几部连载时也写得给人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创造力没有以前那么旺盛了,只是当时还有一个电影在带动著古龙热潮。那时流行的是悬疑性的电影。古龙小说不管早期还是后期,都有悬疑性,拿来改编一下,很容易,所以当时武侠片大都是从古龙原著改编的,还有连续剧,也大都是拍古龙的,很少有其他作家的,因为他们写的小说情节太庞杂了,而且很传统,翻来覆去是什么拜师学艺报仇,没有一种悬疑性。金庸的连续剧是后期才开始拍的,早期台湾还禁他。于是,到古龙死了一两年之后,整个台湾的武侠电影拍滥了,可能观众看腻了,突然之间电影没有了市场。而继续写小说的,也没有写出什么新意来,不仅台湾,连整个东南亚也没有市场了,所有报纸都停了武侠小说的连载,就这样没落了。
张文中:但是在流行文化的市场上,金庸好像还是经久不衰?
薛兴国:台湾最早给金庸武侠小说出单行本的,是远景的沈登恩。在解严之前,他就觉得金庸小说在台湾可以开放了,出廿四开豪华本,卖得很贵,但是市场很好。后来,也有人给古龙出廿四开豪华本,也很能卖。不过,等到古龙去世了,他的电影不放了,他的小说市场也就消失了,唯独金庸的小说还能卖下去。我相信,这种状况跟出版社有点关系,因为远景出了金庸之后,又出“金学研究”的系列,后来又在网站上开辟专栏,有一个宣传效果在那里。而且,金庸的武侠小说,多年来不停地有人拍成电视剧,第一代捧红了周润发,第二代又捧红了谁,现在又捧红了张伟健,金庸还有很多年轻人感兴趣。但是,古龙现在没有什么人在谈论了,古龙小说的出版社大部分是小出版社,就是以前给他一本一本出然后送到租书店的那种,那些出版社现在结束了。然后,古龙又把自己的著作权搞得很乱,他的父亲回来了,继母出现了,这个老婆、那个老婆也出来了,儿子也说他有著作权,谁也搞不清楚。台湾现在的著作权法很严厉,再没有出版商敢碰他的东西。所以,在古龙去世之后,他的小说很少再拍电视连续剧,电影也没有了,他不再成为一个话题。
张文中:因为《藏龙卧虎》的得奖,是不是可能重现新派武侠小说的热潮?
薛兴国:最近好像武侠小说又开始露头了。《联合报》副刊前一阵还连载过张大春的武侠小说,不过太注重历史了。现在还在连载一个新作者的武侠小说,写得不错。不过,我觉得突破一种新的境界的武侠小说还没有出现,所以大概也不会形成什么热潮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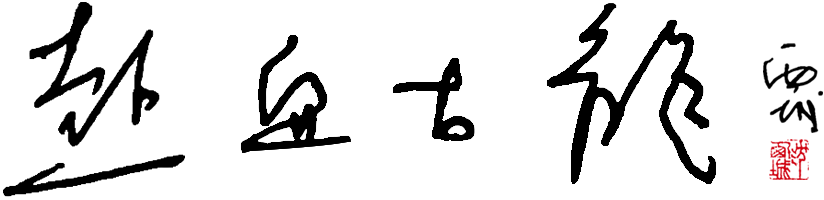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