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步非烟
总序
古人说:一代有一代之文章。
汉赋,唐诗,宋词,元、明、清,曲话小说,各盛一时,民国以来,情、侠奋起于文坛。金、古雄视,温、梁虎踞。还珠帜张于前,黄易翼护于后。极盛之时,街谈巷议,贩夫走卒未能免此,也可算得上一代之文了。
于是,我们不妨用唐诗来比喻上一个武侠大繁荣的时代,这种比喻多少有些闲谈的意味,毕竟李杜和金古都是唯一的。但自古闲谈多妙语,诸君又何妨随偷闲片刻,随我扫半间静室,燃一炉红火,等月透窗棂,风来竹稍,屋内香茶蟹沸,绿酒蚁浮,听我夜话诗中盛唐,剑上金古。
第一夜 陈子昂·还珠楼主
在盛唐灿如星河的诗人群体中,首先凸现出一个身影——在蓟门台上,感慨“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泣下”携琴仗剑的白衣公子。
他叫做陈子昂,正是他一扫六朝旖靡,开有唐一代风气之先。我一直固执的认为,他的泣下中,不仅是感到了独立天地,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苍凉,或许还有一种预言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将要来临,此时此刻的自己独得风气之先的孤独——那是四顾茫然,那是呼之欲出,那是喜极而泣。
很庆幸,武侠的世界中同样走来了这样一个风神潇散的先驱者。他叫做还珠楼主,和子昂一样来自蜀中。蜀江水碧蜀山青,蜀中,历来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峨嵋灵秀青城疏幽剑阁峥嵘锦城风流,似乎都滋养了蜀中才子的一支生花妙笔,以及他笔下极光变幻,天河倒挂的天空;妖莲燃烧,魍魉横行的地下;飞剑神仙,重楼层城的世界。
或者还珠并不仅仅为武侠之子昂而已。还珠有着李白一样汪洋恣肆的笔锋,纵横超拔的才情。将他和陈子昂相比,更多以其对武侠的开创而言。在我们眼中,子昂并不是最光辉灿烂的唐人,但在唐人心目中,他一扫六朝浮华,承接魏晋风骨,有着巨大的功勋。后来诗论家元好问云:“论功若准平吴例,和著黄金铸子昂”。论对唐诗发展的功绩,就该按勾践平定吴国的封赏前例,用黄金铸一个子昂。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要为新武侠的奠基者树立金身的话,还珠楼主也将是不二人选。
第二夜 王维·梁羽生
我要谈到的第二个诗人是王维,第二个作家是梁羽生。
王维出生儒学世家,绘画音律,无不兼通,是最具备艺术家气质的诗人,也是最多传承了魏晋风度的高门名士。梁羽生也具备了深邃的修养以及儒雅的气质,从更多、更深的意义上继承了传统文化,也有着平和优渥的创作条件和心态,年少时也曾诗酒放旷,名满乡梓。因此,梁羽生的作品中,也就更多的表现了一种传统的、平和优雅之美,这正是名士风流,自在雍容。
盛唐衣冠,魏晋人物,是古代文人心中的一个梦,这个梦在王维身上终于圆满。我一直以为盛唐的正音其实归于王维。盛唐诗歌按照应有的轨迹发展,到了王维这里,就是水到渠成,就是正统,就是大成。而李杜的出现,则是上天赐给中国文坛的幸事。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武侠的发展,到了梁羽生这里,也可以算是正统了,金庸古龙的出现,则真的是幸运的异数。
在梁羽生的文章中,未必能找到酣畅淋漓或者诡谲变幻的感觉。未必华丽,未必奇崛,有时甚至会感到枯淡,如今喜欢光怪陆离、诡异变化的年轻读者们,似乎不再欣赏梁羽生了。但是若有时间,一壶清茶,再将梁羽生的作品细细品来,传统而正统的行文之下,也有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闲淡和潇洒。也能体会到梁羽生承继的、更多是民国武侠的济世救人的侠之精神。
当然,这种平和之美不是绝对的,梁羽生和王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一体为主,而又有着多变的风格。而这些在他作品中非主流的风格,放在别人眼中,也高妙得让人震惊。比如王维的诗歌中,也曾有过如此的豪壮:“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九天宫阙开阊阖,万国衣冠拜冕旒。”而如果不喜欢梁羽生冲淡行文的读者,可以去感受一下《还剑奇情录》非同寻常的曲折和紧张。
第三夜 李白·古龙
古龙,是武侠中的李白。一时横绝的天才和纵情诗酒的生活是李白与古龙的共同之处。如果说诗歌史中,李白的出现是让人费解的现象,那么武侠世界中的古龙也是。李白好酒、任侠、古道热肠,四海结交,这正好也是古龙的个性;李白创作上灵光频频闪耀的天才让后人无法临摹其神髓,其实古龙也是。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千年之前,李白写下的这首诗,却成了古龙生活的传神写照。我想,若李白真能穿越了时空,看到后世这死于剑、死于酒的知己的时候,或许李白真会解金貂、换美酒,与古龙一起把盏共醉;又或许,两人只是捻花一笑,而后彻底相忘于江湖。
唐诗中有一个现象,学杜甫,学李商隐的人比比皆是,可是几乎没有人敢学李白。这个几乎当然不是没有,只是学得太差,很难留下姓名。清人甚至讽刺说,学李白学得不像,就成了:“黄狗一飞飞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飞上天,三千年,是李白曾用的词,但不是李白的逸气与傲气,更不是李白本身。与此相反的是,武侠界学古龙的人却是何其之多,似乎只要能断句的人,就敢说自己在学古龙。但谁又有小鱼儿的佻脱,楚留香的潇散;李寻欢的刀,陆小凤的指?如此说来,古人不敢学李,倒是比我们更具自知之明。
终于,当“夜。寒夜。光,剑光”这样的句子,也和“黄狗”“白狗”一样成了一时笑柄,当“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的疑问化为“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的叹惋之时,人间却还留下了这些纷纷俗态。
李白并非不能学,古龙也一样。所谓“功夫在诗外”,如能一剑纵横,千里相思,月歌峨嵋,梦游天姥,渡荆门送别,望庐山瀑布,那也不妨学李;而同样,饮酒过五斗,头大三升,仿佛也可以学古了。
第四夜 杜甫·金庸
集大成而开千流,是历史对老杜诗歌的评价,这句话若形容金庸在武侠中的地位,也是当之无愧。杜甫的成就甚至已用“接鸿蒙”来形容,而金庸也早已是一代宗师,前人之述备矣,只需比较其相似则可。
杜甫和金庸一样,行文中有着恢弘的气势。这种宏大和庄子笔下鲲鹏展翅、扶摇九万里的来自道家的高拔恢弘不同,而是更接近儒家文化的宏大,更深沉,也更浑融,民胞物与,并不仅仅只关心自身的超然。
和老杜一样,金庸无疑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也迅速遍及整个武侠文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话从郭靖口中说出,却给整个武侠定下了“时代正音”,也是侠义之气的正统和典范。无论今天新武侠如何变,但金庸创立的正统始终无法改变,这些有情有义,为国为民的侠客们,也是我们心中一个永远的梦,是我们对武林最正统的想象。
相比而言,梁羽生笔下的侠客虽也是坚守着传统的道德操行的,但是如果非要比较的话,梁羽生似乎逊了金庸一份沉郁浑厚的气势。正如杜甫的诗歌一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间风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这种黄钟大铝之声,不要说今天,就算在那个辉煌的时代也是少见的。而金庸笔下,萧峰雁门关前慷慨就义,杨过襄阳城外射死蒙哥汗的壮烈场面,也达到了至今无法企及的高峰。
另外,杜甫的诗中洋溢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其笔下关乎风月者少,关乎车马烽火者多。这和金庸也是一致的,哪怕在金庸写情最多的《神雕侠侣》中,我们仍然可以从儿女喃呢的间隙中,听到历史的隆隆铁蹄。杜甫虽然历经磨难,但作品中展现的,始终是一片仁者心胸。金庸笔下的侠客们也是。这些侠客们或古板或佻达,但道德的操守是绝不会泯灭的,也许在今天看来有些古板,或许今天的读者们更喜欢更为帅和酷的反派boss,但是所谓“正音”就是说,你可以求变,但你始终无法代替他的位置。
第五夜 韩愈·温瑞安
后世一个同样伟大的文学家苏轼评价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可谓卓有见地。韩愈的人格、修养以及整个的文学成就,无疑是不可争议的。争议的恰好是他的诗歌,这种争议来自他对新途径的开辟,新技法的探寻。也是在这点上,韩愈和温瑞安有了某种共同之处,而虽然两人的优缺点都很多,不是一两段话能说清楚的,但我要谈的正是这一点。
韩愈的特点是以文为诗,用大量散文般的语言去颠覆诗歌的传统,他甚至在《南山》诗中用五十一个带“或”字的诗句来铺排,这种结构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甚至不符合常规的,甚至是对诗歌对称之美、音韵之美的颠覆,但韩愈就是用了。
温瑞安是一个诗人,他的创造正好和韩愈相反,是以诗为文,以诗为武侠。温瑞安小说中经常会有优美的诗歌化的句子出现,就像他的一部小说的名字一样,《刀丛里的诗》。但这还不是最独特大胆的,他和韩愈一样,不仅仅是将一种体裁的优势援引来完善另一种体裁,而是敢于用一种去颠覆另一种。这种颠覆有时候可能带来对传统审美模式的冲击,也可能不被很多读者理解,但是,其中的惊人之笔,却足以铭刻在武侠小说乃至诗歌散文发展的史册上。很多年来,我始终无法忘记,第一次看到温瑞安小说中大段的相同的单字,或者整篇空白时候的震撼。比如,上页的最后告诉你,“他眼前出现一片空白”,当你翻过这一页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片空白。
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百代以下,是否也有人拿来形容温瑞安呢?姑妄言之。
第六夜 白居易·黄易
某一个侧面的李白是通俗的,但他的通俗是清新,用字未必奇,但气象却森然雄阔,气振天下。李杜诗名并骋天下,有唐以后学杜者蔚然,但学李者却盖几希。求其近者,或者白居易稍近之?
然而,与李白的率性天成不同,白居易是用更接近当时以及大众的方式来改造诗歌传统。但他的平易,乃是境界之平易近人,不是宋之柳永的俚语入词。其有诗云:“云霞白昼孤鹤,风雨深山卧龙,闭门追思古典,著述已足三冬。”或者就是他对自己的总结。典雅而悠然。
唐之盛世已到了中晚,开元天宝的盛世到了该由史官追忆的时候,我们迎来了白居易,正如当大武侠时代辉煌的背影已越走越远时,黄易横空出世。文笔并不很高,但一拔而九千丈,化作景天长虹贯然而下。从黄易开始,才真正的是万事万物无不可为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
但或许斑驳正导致杂乱,万事万物未必全可以为小说,从还珠而起,到金庸而将武侠小说拔至的高度,就此崩溃瓦解了。黄易或者是个武侠小说的大师,但仅此而已。从此之后,人们再谈起形而上的武侠小说,就只到金庸而已。
白居易也是求变,他新变的方式是用更接近当时时代以及大众的方式来改造诗歌传统,正如黄易是如此改造武侠传统。
然而黄易不如白居易。白居易的通俗,是为了教化,为了诗歌的社会功用而牺牲它的文学性,但黄易是为了什么呢?是商业。
从这一点而言,两人的新变有着共同的优点,那就是以通俗以及更接近时代的方式开拓了更为广泛的读者。两者缺点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过俗,比如说对传统的破坏。然而,即便如此,黄易仍是位大师,他的颠峰之作正如白居易的优秀作品《琵琶行》《长恨歌》一样,是足以睥睨李杜之后或者金古之后的一个时代的。这些作品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让哪怕不喜欢他的人无法忽视其价值。
第七夜 梦想·李商隐
唐诗有了李杜王孟,是一时之幸,也是万代之幸。而对于武侠而言,有了这样群星灿烂,人才辈出一个时代,又何尝不是?若非要说这个时代有所遗憾的话,我想,是少了一个武侠中的李商隐。
李商隐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伟大决不仅仅局限于华丽幽微的《无题》,转宜多师是他的性格。他学老杜之诗,被人誉为学杜而唯一出其樊篱者,他学李贺之诗,置于李贺集中几乎难以识别,他学韩愈,学李白,学元、白……正是这些,造成了李商隐诗歌丰富多彩的面貌。咏史诗歌中的沉雄劲建,讽喻诗中的深刻犀利,七绝中清新流畅,都是世人一时无法企及的高峰。
毫无疑问的诗,如果只有这些,李商隐也是晚唐的杰出诗人,然是,因为有了《无题》,才让李商隐从杰出变为伟大。
《无题》组诗,代表了李商隐独造的风格。一种风格的形成并不难,甚至说太早形成的风格、太偏激的风格对作者而言有害无益,因为真正的风格是融会后的沉淀,是在吸取了诸家所长后,真正独得于心的创造。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李商隐才是唐诗的集大成者。集大成未必要让自己的诗作中七彩斑斓,闪烁着前人的吉光片羽,若真如此,也不过一件美丽的百纳衫。“集”之后是“成”,成就的是一种贯通之后的浑融,成就的是个性化的自由抒写,是天才的创造。这种创造汇聚百川,却又带着如此鲜明的个性,它属于李商隐,并且只属于他。
然而,武侠中并没有出现李商隐这一派的大师,至少现在还没有。这使得后来学习华丽幽微这派文风的人不得不去求助没有写过武侠的张爱玲、李碧华。没有前代范本,本已让这种学习充满艰辛,而他们却又犯了和学习李商隐诗歌的人同样的毛病——他们的学习仅仅限于《无题》。殊不知,只从《无题》去学习李商隐,那么一辈子也写不出《无题》。
因此,那些的作品空有李商隐的辞藻,而没有李商隐的积淀与浑融,也就只能算做剑走偏锋的西昆体,而非义山正宗。面对如此局面,我们只能再次感叹,武侠中少了这样一个华丽但深邃,隐幽但浑融天成的李商隐,是大武侠时代的最大遗憾。
幸好,这遗憾,也就成了我一个异代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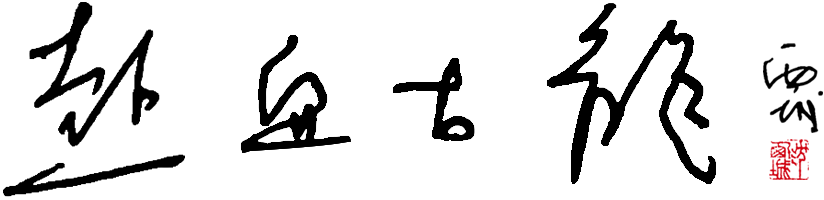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