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今古說武俠》(林保淳 著),五南文化事業出版,2016年7月
從發願鑽研武俠,到實際展開研究,到本書的集結,一晃之間,二十五年就匆匆過去了。
我還深深記得,那就是在我博士班口考通過的當天。在歷經一場緊張但還算順利的答辯,然後喜沖沖的趕去參加楊儒賓的婚禮之後,在回程的路上,我慎重且嚴肅地思考自己的未來。
取得博士學位,歷時和抗戰一樣,整整八年,如此漫長的時間,對我來說,究竟有何意義?從小,我深知自己的個性是好強、任性,不受既定框架拘管的,以此,敢於冒險,勇於精進,但也與世多忤,在師友間頗蒙叛逆之譏;而疏於人際,直言讜論,更在有意無意之間,開罪不少人。儘管在學業上我戮力以赴,未嘗遜色於同儕,但面臨未來的職缺問題,也頗心知肚明,能僥倖得一枝之棲,就算是蒼天獨厚的了。然則,我何去何從?應該走何種路線,規劃我未來的研究領域?
當時我是有三條路線可選擇的。一是賡續我碩、博士的研究方向,再接再厲,在故紙堆中奮鬥,探索古代的文學思想及理論,這是我的「正業」,也較易於穩紮穩打,累積出若干成績。這對我而言是可以駕輕就熟的,畢竟,十數年來的努力多少也不至於虛擲。但是,我總是會考量,古人的精言高論,固然對我啟迪甚多,且鑑古足以知今,深造之,亦能自得之。可是如不能古為今用,終究還只是關在象牙塔中的學問,於人於己,了無真義。
二是選取當時方才崛起未久,而未來勢必成為顯學的台灣文學研究,這是一條新路,而且我自小深受姑丈吳濁流的濡染,說來也算是名正而言順。而且,身為台灣人,自當通曉台灣事,台灣文學向來為學界所忽略,以此作開展,也未嘗不能有所樹立。不過,當時的風氣,多籠罩在一股濃厚的政治氛圍中,我素來對政治極為厭惡,雅不願沾惹一身腥羶,對此自是敬而遠之。
三是選取我自小就深深喜愛的通俗文學研究。這條路顯然是最坎坷的,因為通俗小說向來被目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致遠恐泥,達人君子,何屑於為?而且草萊未闢,遍是荊棘,頭緒萬方,又當從何著手?但是,所謂的文學,難道就應該排擯為眾多讀者所喜愛的通俗說部嗎?在我心目中,文學不應該只是文人學士案頭筆下所獨享獨得的,引車賣漿者之流,亦自有其可以步入文學殿堂,窺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的權利,而通俗說部,淵遠流長,亦已證明了其應有的意義與價值。當學者津津樂道於古典「四大奇書」及《紅樓夢》的偉大藝術成就之時,又焉知後之視今者,不會將當代的通俗說部,如武俠小說中的金庸、古龍等人作品,視如瑰寶?自小,我就是閱讀武俠小說成長的,雖不敢自謂能探驪而得珠,但卻對當時一面倒的批判武俠之聲,難以茍同。事實上,我是很早就對武俠研究感興趣的,在甫進碩士班時,就曾跟業師吳宏一先生提出欲就武俠小說的課題展開研究的意向。吳老師對武俠的觀點,是與當時學界大不相同的,當初我在大學修習他的「小說選」課程時,他就曾刻意標舉武俠小說的重要,對我啟迪之功甚大。可以說,我的武俠研究之路,是在吳老師引領下導生而出的。他也深知我對武俠小說的興趣,大概能力上也還能蒙他肯定,因此,在1981年,柏楊先生編纂《一九八○中華民國文學年鑑》 時,原擬由他執筆的評介武俠部分,就轉介由我執行,這也是我第一篇寫的有關武俠說部的評論。不過,當時未蒙吳老師首肯,想來應該是為我設想,唯恐我冒險涉難,走上一條不為學界所認可的武俠研究不歸路。我是深知當時學界風向的,也能預想到我萬一走上了這條路,所將面臨到的是如何排山倒海聲勢的壓力。但是,由於我個性上的好強與彆扭,再加上我對「文學」二字的認知,當時我想到的是龔自珍「亦狂亦俠亦溫文,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詩句,梁啟超、胡適既深受此語感召,我又何嘗沒有這膽量去揭竿而起,就充當著通俗文學研究中陳涉的角色?即此,我當時未有多少踟躕,就毅然決然的,風蕭蕭兮易水寒,懷著雄心毅力,挾著鏽刀鈍劍,起錨了我的江湖行程。
就在我獲得博士學位的那天晚上,我在漆黑的夜色中,寫了一封給幾個武俠出版社的信,請索他們所出版或經銷的武俠書目――我始終認為,建立書目、作家檔案,是武俠研究的基礎――這算是我所發的第一張「英雄帖」了。
我非常渴慕古龍武俠小說中英雄惺惺相惜的場景,道路相逢,傾蓋可以定交,一生可以無違。江湖路上,我雖未算得道,但卻也可以說是多助的了。葉洪生先生是第一個仗義相助的好漢。
我和葉先生的因緣,早在我讀書時期看他的武俠評論就奠定下了,他可以說是台灣武俠研究者的第一人,就在一次我主動約訪,細論長達六小時不歇、猛吸多達三四包煙的淋漓下,蒙他不棄,就此定交,大有沈浪和熊貓兒的酣暢。葉先生胸懷坦蕩,俠氣縱橫,拔擢後輩不遺餘力,我自是沾丐不少。其後我倆遍結英豪,如張贛生、嚴家炎、徐斯年、陳墨、岡崎由美等俠友,都可謂是一見如故,作了「煙俠舊友」(唯嚴先生不吸煙)。葉先生與我合著了《台灣武俠小說史》一書,頗蒙學界好評,全書由他通稿,功居第一,我附驥尾而行,也覺沾光不少。
龔鵬程先生與我相識近40年,援引我入淡江大學中文系,交辦的第一件事就是籌備一場「俠與中國文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龔先生學富五車,識見精到,對武俠亦是傾慕有加,早年即以《大俠》一書暢論俠文化,至今猶為研治武俠者的圭臬。我們合編了《二十四史俠客資料匯編》,成立了「中華武俠文學學會」,合作過難以計數的文化策劃項目,是同儕中與我甚為相得的盟友。我在淡江的「武俠研究室」得以成立,他的臂助之功,是不能抹滅的。
在這二十幾年當中,識我知我者,頗不為少,但暗潮洶湧處,也是浪駭濤驚的。說有排山倒海的壓力,也許太過誇張,但是,師長的側目、友儕的嘆惜、不知我者的嘲訕、識見狹隘者的鄙夷,我是看得太繁、經得太多了;但我沒有退縮,更不能卻步,「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對我而言,武俠研究是條不歸路,蓽路藍縷,能走多遠,算是多遠;呼朋保義,能拉多少,算是多少。即便是拔劍四顧,形單影隻,我也未曾後悔、遲疑過。所可懟者可愧者,是自己學力不足、努力不夠,因此有遺有憾,至今猶未能開闢出當初我想建立的一套通俗文學理論體系。
本書所收,是我進入教界後所發表的一些論文及長短不一的武俠相關評論,有些曾經發表,有些則未經披露。由於論文撰寫時,各種期刊與會議所要求的格式不一,因此在注解體例上有若干出入;而且篇中所論,為求其首尾貫串,往往不得不援舊說以入,因此偶爾會有重複的文字,但是為保持原貌,覶縷出我這二十幾年的思考方向及觀點,除了重複太多的予以割捨、刪削外,多數是「率由舊章」的,如有沓冗累贅之處,還請讀者見諒。書名《縱橫今古說武俠》,顧名思義,有縱有橫,不拘一格;論今議古,卮言漫衍;而全環繞「武俠」二字開展,知我者,罪我者,其於此書乎!
這篇序文,只略述我研究的心路歷程,有關我武俠方面的觀點及研究的成果,是書所收,應足以呈顯,在此就不贅言了。我最早出版的武俠專著,是《解構金庸》一書,未來擴充其內容,因此本書除〈金庸臥龍相對論〉外,暫時不收金庸小說的評論,讀者可以參看《解構金庸》。
最後,要感謝老龔替我寫了多所揄揚的序文,不過,除了內中說我「懶」是正中其弊外,其他的溢美之辭,就不必太過認真了。是為序。
2016林保淳於說劍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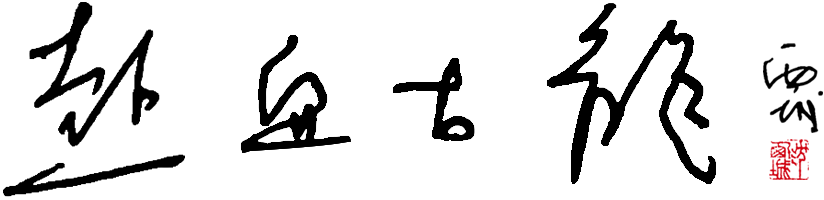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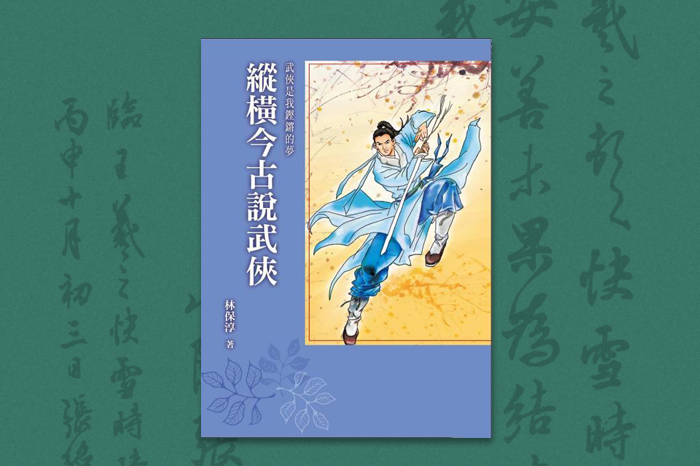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