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小說新解》,林保淳、黃東陽編著,國立空中大學出版,2021年
「唐人小說」是我大學時代中文系學生幾乎必讀的書,這不但是因為其中各類型的小說往往都有相當高的古文水平,且亦充滿著各種趣味盎然的故事,於向來主要以載道為主古典文籍中,別具一番思致;更是由於若是未能稍微熟諳其故事內容及所表現的文學技巧、思想觀念,就可能完全無法真正了解後來小說與戲曲的發展源流;因此,人手一冊,展卷而讀,雖說深淺不同,各有所得,但對其中的名篇佳文,莫不都耳熟能詳,可以津津樂道。
不過,晚近以來,學風丕變,學子目古文為八股,視古典為贅疣,多數大學中文系已不太開設相關課程,即便偶有開課,也往往只有寥寥可數的學生選修,而原本坊間隨時可買得到的讀本,無論是汪辟疆或是王夢鷗的,也都未必能夠洽購,選修同學甚至連買也不肯買,故學子渾不知南柯枕中為何事,鶯鶯小玉為何人;隱娘紅線,無以炫其技;子春老父,不能言其慨,非煙飄散,任氏離魂,寖至譚嗣同的絕命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都能解釋成杳邈難及的崑崙山,古道既不能照顏色,風簷又何可展書讀?
當然,這也不能夠完全歸咎於學生,整個社會的風氣如此,文言、白話斬然分為兩截的觀念,已是積重難返,學子受其誤導,以為文言文是死的文字,與現代社會格格難容,卻忽略了,文言文是文學的語言,與一般日常生活中的白話口語是有區別的,古人日常說話,自然有另一套體系,除非冬烘老朽,任誰也不會在日常生活中專用文言,這就是白話。白話文當然也能夠發展出其自有的文學語言,古典白話小說的文學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民國以來的白話文運動,最大的貢獻在於從此擺脫自古以來獨尊文言、輕視白話的固陋觀念,而開展出現代白話文學的新頁。事實上,古典白話小說雖以白話為基礎,卻也參酌了文言文的精煉造語方式,文白揉合,才能夠雅俗共賞的。文言與白話,絕非想像中是冰炭不容的,就是在我們日常的言語中,也常能發現其相互揉合的現象。白話文言,各有所長,以白話的靈活流暢,濟之以文言的典雅精煉,又何嘗不能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將文言與白話判若鴻溝,其實是相當荒謬的。
更何況,中國傳統文化,幾乎都是以文言文寫成的,相關典籍,汗牛充棟,自不能全數加以譯介成白話,能夠熟諳文言窾竅,則可不假外力,自我學習,這對中文系的學生而言,更是格外緊要。唐人小說可謂是文言文中的精品,自來有「史才、議論、詩筆」三者合一的高度評價,與一般高頭講章式的古文有異,能藉恢怪瑰奇、趣味盎然、思致深沉,乃至纏綿悱惻的敘事內容,引領我們置身於「傳奇」多姿多采的想像世界,在我看來,除了可以藉此進窺中國傳統文學、文化的堂奧外,更可以作為研習古代經典的階梯,擯而不讀,實是中文系學生莫大的遺憾。
唐人小說篇章甚多,李劍國的《唐人小說敘錄》,已是洋洋大觀;而汪辟疆、王夢鷗的精挑細選,也還是琳琅滿目,雖說考據源流、剖析肌理,都各有所長,但畢竟猶嫌其繁多;且其書以供學者研究為主,故全無註解,這對現代學子而言,的確是一大閱讀障礙。因此,於其中再披沙揀金,無疑是相當必要的。黃東陽教授與我合寫的《唐人小說新讀》,既是為了空中大學新課的教科書需求而撰,也是想精益求精,甄選名篇,分類部居,並酌加註解,提供學子一道入門捷徑而作。
書名「新讀」,其實也未必有多「新」,畢竟,所有的「新」都是奠築於「舊」的基礎上而成的,才疏學淺,自然也不可能有多少翻新出奇、駭人耳目的「新解」,但我們儘量從若干可能前賢未能關注或言之而未詳的角度,作一番自我的解說。其所「新讀」,或許可能是種「誤讀」,但提供若干不同的解讀,似更可證明唐人小說具有豐富的內容及可以拓展的空間,這豈非也是文學研究最大的樂趣所在?
唐人小說由於是從各不同載籍中撮抄而來,其間因所據版本不同,文字各有參差,本書全文,以王夢鷗的《唐人小說校釋》為準,這是學界所公認的善本,料想應是足以憑據的。
《唐人小說新讀》的完成,有賴年輕而具有實力的黃東陽教授襄助,雖云「襄助」,其實他所付出的心力,實遠超於我,在此特致感謝之忱,書中所解,如有一得之愚,理當歸功於他;而其荒疏妄誕之處,則其咎在我,還望學者不吝批評指教。
庚子六月林保淳序於木柵說劍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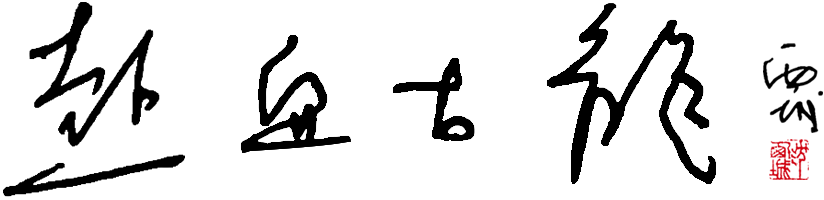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