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龙传》(覃贤茂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
古龙达到了武侠小说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这个高峰讫今无人能够逾越。
古龙改变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方向和技术,古龙的影响是前无古人的。
到了古龙人们才发现武侠小说居然可以这样来写,而且可以写得这样的神妙。
古龙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武侠小说的形式的天才的洞察、领会和把握,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与构造小说形式的能力极为罕见地完美结合起来的批判的智力。这些批判的智力内在地驱动着他去“求新求变”,使他对武侠小说艺术的形式保持着一种天才的敏锐触觉,对形式和构造作出最精致得当的探索。
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的序中说:“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如果真是由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至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到达巅峰,至王度庐的《铁骑银瓶》和朱贞木的《七杀碑》为一变,至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又一变,到现在又有十几年了,现在无疑又到了应该变的时候。”
古龙已经看出了当时到金庸为止的旧派小说的弊病;旧派武侠小说的成熟的结果必然是腐朽和僵化,旧派武侠小说已经起来越缺乏新意,越来越公式化,模式化。正如古龙所指出的:
“武侠小说的确已落入了一些固定的形式。
一一个有志气,“天赋异禀'的少年如何去辛苦学武,学成后如何去扬眉吐气,出人头地。
这段经历中当然包括了无数次神话般的巧合与奇遇,当然也包括了一段仇恨,一段爱情,最后是报仇雪恨,有情人成了眷属。
——一个真正的侠客,如何运用他的智慧和武功,破了江湖中一个规模庞大的恶势力。
这位侠客不但“年少英俊,文武双全?,而且运气特别好,有时甚至能以“易容术”化妆成各式各样的人,连这些人的至亲好友、父母妻子都辨不出他的真伪。
这种写法并不坏,其中的人物有英雄侠士,风尘异人,节妇烈女,也有枭雄恶霸,荡妇淫娃,奸险小人,其中的情节一定很曲折离奇,紧张刺激,而且很香艳。
只可惜这种形式已写得太多了些,已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而且通常都写得太荒唐无稽,太鲜血淋漓。”
古龙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相当响亮的口号:“求新求变”。
“求新求变”的精神拯救了已趋于僵化和大而不当的武侠小说,也拯救了作为武侠小说作家的古龙自己。
虽然古龙具有超乎常人的艺术天才,但如果他没有求新求变,他的那些卓越的天赋最多只能把他造就成上官鼎、诸葛青云、柳残阳的这样的一些武侠小说的高手,或者是金庸的一个传衣钵的学生,而不是一个自成一统的大宗师。
古龙内在的批判的智性使他的天才发出了真正夺目耀眼的光芒,使他的艺术生命变得辉煌壮丽。
只要我们考查一下古龙创作的当时的武侠小说的背景,就可能看出古龙的成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古龙试笔创作的60年代,正是旧派武侠小说登峰造极的全盛的时期,旧派武侠小说完美得几乎无可挑剔的光芒淹没了整个武侠小说的王国。
在这个时期,香港方面的梁羽生已名满天下,写出了《龙虎斗京华》、《萍踪侠影录》等武侠名篇,一炮打响,拉开了自民国时期之后旧派改良武侠小说运动的大幕。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发展到40年代末,已经是强弩之末,势必需要二种更美的形式和特质给旧派小说注人生命力。梁羽生适逢其时,以个人禀赋特异的才能拯救了旧派武侠小说。
紧随着梁羽生的成功,金庸不甘寂寞,却又后来居上。以他的雄才大略和磅礴气概将旧派武侠小说改良和发展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峰,金庸写出了《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等无与伦比的巨著,金庸出手不凡,佳构泉涌,一部《射雕英雄传》,奠定了他不可动摇的武林盟主和大宗师的地位。
金庸在1964年,已经完成了包括《射雕英雄传》三部曲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在内的十大部辉煌巨著,而古龙这个时候连《大旗英雄传》还没有写出来。
古龙还没有出道,面前就已经是无数难以攀援的绝顶奇峰。
而在台湾方面,旧派武侠小说的发展也是云蒸霞蔚,如日中天。60年代是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的全盛时期,武侠小说作家多达三百余人,台湾武侠小说四大门派,前三派:“超技击侠情派”、“奇幻仙侠派”、“鬼派”一直占据了主要的武侠小说市场,还有一派新派是古龙所创,已是后话。
古龙在那时才刚人道,而诸葛青云、卧龙生、司马翎这些武侠小说作家却已拥有了很大的声誉,据说这些大侠们常常聚在一起打麻将,一边打牌,一边神聊武侠,每天在各大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古龙则是在一旁侍候,等这些大侠们有时牌兴正浓来不及写稿时,便让无名小卒古龙去代为捉刀,续上几段。这些大家的声望已经塞满了名誉的整个空间。
此时的古龙不过是替那些武侠名家端茶倒水的无名小辈,这对古龙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平衡的处境无可言说而深刻痛心地刺激了古龙,而且这种扼腕之叹也成了古龙一生的难解情结之一。
光荣和梦想的本能激动着年轻气盛的古龙,一场内心的风暴正在古龙的胸中汹涌不息地掀起。
如果不能求新,不能求变,不能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去否定、推翻,代替陈旧的武侠小说艺术形式,古龙还不如不写的好。
这样的一个尖锐的矛盾当然不是仅仅存在于那个时代古龙一个人的心中,当然还有无数的不满意者内心在渴望着去打碎那个既得利益的旧世界,使一代人都获得新生。
也就是说,物极必反,当时的时代也在呼吁一个求新求变的新的武侠天地的诞生。
最早倡议“新派武侠”的是台湾的作家陆鱼,陆鱼的《少年行》可以说是开了与旧派武侠小说唱反调的先声,陆鱼作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是这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武侠小说既成的模式的感染力太强大,这种顽症决不是一针一丸能治疗得好的。
这个时代的重任偶然而必然地落到了古龙的肩头,他既生逢其时,又有一种天赋的批判的智力和构造的智力,他在批判旧派武侠小说的弊病的同时,构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武侠艺术形式。
古龙当时的难题是:要当一个武侠小说家,就既不能重蹈“超技击侠情派”、“奇幻仙侠派”、“鬼派”的轨迹,也不能去仿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金庸和梁羽生,他必须另出奇招,再辟蹊径,写另外一种完全与既有模式不同的武侠小说,这样他才能避免被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大师们的名气所湮没。
古龙反对旧派武侠小说的写法,不仅是内心的情结所促成,也是形势所迫,时势造英雄。
要想获得真正的成功,修成金身正果,古龙的眼光自然要对准金庸。
这是一双批判和挑剔,存心找岔,精明狡黠而又略带一丝妒忌的眼光。
金庸已经成为了整个旧派武侠小说的代言人和无法逾越的高峰,由于金庸拥有了一种温柔、敦厚、博大细致、精力充沛、沉着稳健、高屋建瓴的无限智慧,金庸统治了当时武侠小说的王国,无人敢撄其锋。
金庸浩大全面精确的结构,细致格物的描写,纵横充溢的想象,学贯古今的厚实,无疑征服和倾倒了无数英豪。
但是如果以古龙挑剔的带着种夸张的机智的眼光来看,金庸的小说却是固步自封的,束缚人们的思想的。
“侠之大者”的高、大、全形象,往往又容易落入假大空的圈套,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对于众多的世俗凡人的读者,也会流入大而不当,金庸的小说语言对整体结构的重视和过于细致的“格物”,也影响了一种空灵、飘逸的神韵艺术境界,落入尾大不掉的之中。阶级的理想有时候并不关注于个体的创伤和愿望,个体的心灵同时也需要一种关注自由和生命本身的哲学思想的抚慰。
古龙就是这样在对金庸的景仰中看待金庸的这一切被放大的弱点,他把这些有益的挑剔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念,他所关心的是金庸的作品阳光所未照到的地方,他把握了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金庸给后来者无意地留下来的光荣的机会,他要走金庸的脚迹所未踏到过的地方,从金庸停止的地方开始起步,去发现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古龙超越了金庸、补充了金庸,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给予古龙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份。
金庸写了侠之大者,古龙写了侠之风流。
金庸写了侠之史诗,古龙写了侠的内心的历程。
金庸是厚重博大的,古龙则是轻灵、飘逸。
金庸关注的是阶级的理想,古龙侧重的是心灵自由的雅望。
古龙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的确是可以毫无愧色地与金庸并列为两大难以超越的绝顶奇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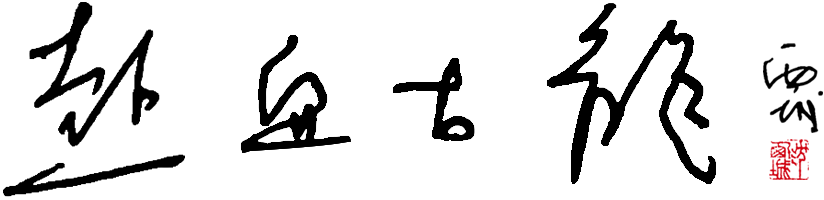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