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序,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武俠小說不是藝術?
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九二〇年代之後,先有平江不肖生向愷然的表彰俠烈,重振墜緒;繼有還珠樓主李壽民的馳情入幻,另開新境;然後王度廬、鄭證因、白羽、朱貞木等名家輩出,蔚為大觀。而顧明道以古樸自然的文筆,歛放自如的情節,崛起於平江、還珠之間,也曾一度享有盛譽。迄於一九五〇年代,後來居上的金庸,挾其靈動雄渾的大筆、超妙入微的想像、西洋文學的技巧、深度人性的體驗,為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創造了嶄新的高潮。
近代中國武俠小說與清代習稱的俠義小說之間,有其承傳的淵源,但也有變異的特徴。
就承傳的一面來看,兩者同是中國民俗文學中,以江湖人物與武術技擊,為刻劃對象或表意媒介的作品,但就變異的一面而言,武俠小說中的武術技擊,已逐漸演變為純粹的「道具」,不具有若何寫實的成份(鄭證因例外),而所有言情小說、諷刺小說、譴責小說,乃至神怪小說中的内涵與特色,卻逐漸溶入到武俠小說的體裁之中。於是,失去了寫實意涵的武俠小說,反而形成了一個極其特殊的文學類型,因為整個的武俠世界(江湖、武林),恰恰幻化為一個典型的象徵結構,可以表達出寫實主義的文學作品相當不易處理的若干题材,例如人性的極限、生死的衝突、權力的鬪爭、命運的可怖、悲劇性的掙扎等。
在這一段武俠小說的興起與演變過程中,末俗濫惡的作品,當然比比皆是,但自成風格、迥異流俗的作品,卻也不在少數。誠如義大利美學巨擘克羅齊(B.Croce)所言:「任何作品,只要是成功的,便是藝術;否則,便是糟粕。」藝術與糟粕的分野,本不在於作者採用的媒體、素材或文類之不同,而在於表現的風格技巧,探及的人性深度等,迥然有異。近代中國的武俠小說,平心而論,不乏成功之作,只要不是心存偏見,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將民俗文學的這一支深受社會大眾歡迎的流裔,擯拒於未來中國文學史的範疇之外。
「俠出於偉大的同情」
武俠小說是否有人文精神或現代意義可言?它的流行是否只代表一種集體心理上「逃避現實」的趨向,因而必然只能是中國現代化的負面因素?恐怕是一個不能籠統判定的問題。近數十年來,哲學界、人類學界與心理學界,已開始注意到遠古神話中可能蘊涵的人文精神與現代意義,而不再只將神話視為悠謬荒誕的迷信或愚味。這對於人們的思考事物的視野與角度,無疑提供了一項有力的糾正,一種反省的方向。
武俠小說的内容,誠然帶有不少悠謬荒誕的成份,然而,武俠小說的内容並不僅止於悠謬荒誕,若干名家的用心工作,尤其深具追尋生命意義、批判現實社會的寓意。企圖利用「俠」的光明形象,來表述理想中的人格境界,或利用「俠」的奮闘歷程,來描述人間世的層層弔詭。真正能够引起共鳴的武俠作品,大抵均能深契於羅家倫先生當年對「俠」的現代意義之闡發。羅家倫曾特意指出:「俠出於偉大的同情」,是一種深然忘我的高貴情操,也是一種生命意志的自然流露,一個沒有俠氣的社會,經常流於殘忍刻毒、頹廢慵懨。倘若我們不認為在現代化的社會之中,殘忍刻毒、頹廣慵懨仍是一種必須超越的心態或行為,則我們也許可以認為武俠小說所標榜的「俠者」的典型,所抒寫的「偉大的同情」,已全無現代意義可言。然而,事實上,理想的現代化社會,絕不只是一套「合理化」的體制與一群「高效率」的人眾而已,同情、諒解、公平、正義等深具人性色彩的欲求與表現,仍將是現代化社會,絕不只是一套「合理化」的體制與一群「高效率」的人眾而已,同情、諒解、公平、正義等深具人性色彩的欲求與表現,仍將是現代化社會的評估指標之一,此所以武俠小說的内涵,未必全然與現代化的理念格格不入。
反抗是人性的肯定
進而言之,武俠小說所强調的俠者精神,基本上是一種向不公道的命運或體制抗爭的精神,是一種不對無理的控制或播弄屈服的精神,它的人文意義其實十分豐表。當代存在主義的著名代表者之一,法國的人道主義作家卡謬(A.Camus)在他精意覃思的名作「反抗者」(The Rebel)之中,曾將這種精神的哲學意義與現代情境,作了鞭辟入理的剖析。他指出:向不公道的命運或體制抗爭的人,本質上是要維護人性深處最後的一點尊嚴與價值。反抗者雖然拒絕了某種外在的安排,但正由於他具有反抗的精神,所以絕不會流入虚無主義,因為他在頑强地證明他内在有其「值得珍惜」的事物,有其「不可放棄」的人性價值,例如對自由的期欲、對正義的執著、對公平的嚮往。到了極限之處,倘若他不能維護這些價値,則他寧可接受毁滅,接受死亡的命運。卡謬認為,由於現代社會的集體性格,往往淹滅了個人價値,極權主義的恐怖陰影,隨時可能迫人而來,所以反抗的精神,雖然在原則上必須謹守在自身應有的界限之内,而不可忽略了個人生命與社會體制之間的分際所在,但在某種意義下,反抗的精神正是人性存在的表徵,因為反抗正是不妥協地肯定人性尊嚴的可貴,故而具有强烈的現代意義。
武俠小說所强調的俠者精神,與卡謬心目中的「反抗者」精神,當然仍有一定程度的區別,畢竟,卡謬對「反抗者」所作的反省與分析,是針對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與現代情景發言,與中國的「俠」之理念初不相干。而一般武俠小說作者,也未必能自覺地强調偉大的同情,反抗的精神,或人性的尊嚴。然而,我們若逕視武俠小說之所以廣受民間歡迎,只是一種集體心理上「逃避現實」的趨向,則未免對各項複雜而相關的心理因素、歷史滄桑、時代背景,作了過份簡化的解釋,而無法看到另一面的真相。正如我們若不經卡謬的剖示,便很難想像代表消極或破壞意義的反抗,原來正可能是人性深處最積極的肯定。
無論如何,真正高明的武俠小說,必定要觸及到人性深處的某些特質,正如任何真正高明的其他小說一樣。惟有從這樣無所偏頗的立場著眼,才能給予武俠小說以適當的評價。
武俠小說的兩大流派
近代中國的武俠小說,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揭開序幕之後,立即就有還珠樓主李壽民以不羈之才,生花之筆,推出氣勢浩瀚的《蜀山劍俠傳》,為民俗文學煥發了出人意表的異彩。從一九二〇年代至四〇年代末期,武俠小說已從滬上、平津等通都大邑出發,逐漸風行於大陸各地。這期間雖有不少駁雜不純的作品與倏起倏滅的作者,應時而興,但大體而言,如顧、王、鄭、白、朱等名家,確是各具特色,屢有佳構,或以敘事古樸見長,或以寫情婉約取勝,或發揚俠烈至性、生死無悔的情操,或傳述武術技擊、江湖幫會的故實,或引介邊疆民俗、豪客異行的傳奇,為武俠作品開拓了一片遼濶的天地。而尤以平江、還珠為個中翹楚,雙峯並峙,二水分流,作品既多,傳佈又廣,在讀者羣中建立了歷久不衰的盛譽。
平江與還珠兩人,恰恰代表了近代中國武俠小說領域内,「入世」與「出世」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走向。平江初撰《江湖奇俠傳》時,對自己作品所要强調的精神内涵,似尚沒有清晰的自覺意識,所以摭拾了民間械闘、幫派火讲、清末軼事、少林掌故、江湖奇談、劍俠法術等各項不同傳聞,只求生動熱熾,不免牽合拼湊,但敘事繁而不亂,佈局亦甚巧妙,一卷成名,並非倖致。等到續撰《近代俠義英雄傳》之時,平江對亂世之中俠義人物的行誼,已有自覺的表彰與强調之意,所以他自譚嗣同從容就義寫起,隱然推尊譚嗣同為一代儒俠。從譚氏「絶命詩」中「去留肝膽兩崑崙」之句,引出清季豪俠大刀王五,繼而詳述大俠霍元甲的一生事蹟,最後以日人設謀毒害霍元甲作結,表達了强烈的抗日愛國情操,全書確有强調民族氣節、表彰俠烈精神的命意。此所以當時上海名士沈禹鐘在為此書所作的序文中,逕自認為平江繼承了太史公「游俠列傳」的遺意,並慨歎世衰道微,禮失在野,激昂慷慨游俠好義之士,反而在苦難中努力實踐了儒家的淑世理想,所以「俠之為道,蓋貌異於聖賢而實抱己飢己溺之志者也。用雖不同,而所歸則一。」沈氏甚至推重平江苦心傳述軒奇俠烈之事,「奇情壯彩,栩栩紙上」,其表彰游俠、發揚義烈的功勞,可以與司馬遷、施耐庵先後輝映。
將平江不肖生比擬於司馬遷、施耐庵,雖然是不虞之譽,但平江如此自覺地以通俗文學的情節内容,來刻劃與抒寫俠義人物的精神和行誼,卻的確為後來的武俠小說指引了「俠」重於「武」的基本方向。平江之後,「入世」一系的武俠作者,在文字技巧與情節構思上青出於藍者,頗不乏人,但凡以負責態度從事武俠小說之創作,而能獲得廣大讀者接受與欣賞的名家,大抵均不曾偏離平江表彰游俠、發揚義烈的基本方向。
還珠樓主的奇峯突起
至於「出世」一系的代表人物還珠樓主,實在是近代民俗文學作者中的一位奇才,其長達四百餘萬言的《蜀山劍俠傳》一言,寫景之落英繽紛、敘事之曲折離奇、談玄之超妙入微、述異之奇幻詭譎,固在在令人有驚心動魄、目不暇接之感,而構思之超曠涉虚,氣勢之浩瀚磅礴,尤其有如天風海雨,迫人而來,魚龍曼衍,無窮無盡。
通體看來,還珠的作品直似「七寶樓臺,炫人眼目」,而拆散細看,則每一片段都仍有其可觀之處。無論是劍俠飛仙、靈禽怪獸、山精海魅、神兵利器、奇珍異寶、天府冥域,抑或是由這類要素交織而成的正邪鬥法、天人交戰、應劫超昇等奇幻情節,無不顯示了還珠本人噴湧的靈思、龐駁的雜學、恣縱的想像與特殊的才華。透過《蜀山》及相關的作品,還珠樓主創造了一個完全超現實的神奇世界,而儒釋道各家各派的思想、境界、與名目,均被他以活色生香、歷歷如繪的文字,溶入了這個超現實的神奇世界。若要勉強追詰《蜀山》在中國民俗文學傳統上的淵源,則《封神演義》、《西遊記》庶幾近之,但在想像的豊富、包羅的繁雜與文字的逼真等方面,儼然有今勝於昔之勢。而正因為還珠樓主的博學與妙才,戞戞
獨絕,迥非任何學步者所能企及,結果《蜀山》等書,雖開創了近代武俠小說的「出世」一系,但孤峯自峙,無以為繼,後來雖也有模仿還珠而撰寫「劍仙小說」、「劍俠小說」之類的作者,由於不具備還珠的條件,大體均遭到自然的淘汰。
時代變局下的遭際
平江、還珠之後,直迄一九四〇年代末期,武俠小說風行於中國境内,浸假而有成為近代民俗文学的主流之態。其間極有潛力的作者,雅俗共賞的作品,方自一一陸續出現,然而,時局丕變,戰亂流離,整個民族一時陷入於空前未有的大動盪中,於是,這股正待發皇伸展的民俗文學的流向,頓時戞然而止。事實上,與整個大時代的動亂相形之下,平江、還珠等人以降,近代武俠作者聲名逐漸湮沒、創作全然中止、作品也多告散亡,不過是一抹小小的漣漪而已。直到十年之後,港臺兩地新興作家蔚起,金庸開創了新派武俠的蹊徑,將西洋文學與戲劇的技巧,引入到傳統武俠小說之中,轟動了港臺星馬等海外的華人社會,武俠小說才回復了生機,終致再度掀起熱潮。
王國維的文學眼光
昔海寧王靜安先生,有感於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如楚騷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宋詞等,均有完整的傳本,而為後世所推重,唯獨元人散曲,因為「為時既近,託體稍卑」,各項載籍均不著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以致於「一代文獻,鬱堙沉晦」,達數百年之久,故而發憤蒐集資料,編成「曲錄」。
元人散曲起自民間,「託體稍卑」,正是民俗文學的特色,但王靜安先生認為他本人讀元人雜劇的感受,元曲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所以即使學界不予重視,他本人「痛往籍之日喪,懼來者之無徵」,不惜毅然從事這一民俗文學的考訂工作。從「曲錄」到「宋元戲曲考」,王靜安先生在研究戲劇源流方面的學術成績,固然公論久定,長垂典範;他重視民俗文學的遠見卓識,即使在如今看來,也仍是令人欽佩無已的。
作為民俗文學的流裔之一,武俠小說雖然不甚可能如元人散曲一般,够資格代表「一代之文學」,但根據王靜安先生的說法,至少「託體稍卑」並不構成武俠小說不能在民俗文學統緒中佔一席地的理由。不幸的是,近代中國武俠小說的遭際,遠較當初的元曲更為鬱堙沉晦,除了一九五〇年代之後,流行於海隅的作品之外,早期風靡於民間的作品,不待時間的淘煉與「儒碩」的「鄙棄」,一場政治動亂就已使它們陷入到近乎萬劫不復的絕境,因為蓬飄煙消、散佚錯亂之後,絕大部分的作品,已隨著作者本人的亡故或輟筆,而化為一堆刧灰了。
「武俠小說名著大系」
如今,葉洪生先生有感於此,認為:要對武俠小說給予適當的評價,必須先還原那些已經蓬飄星散的近代名家作品,於是在對早期武俠名家初步作過有系統的介紹工作,並撰為《蜀山劍俠評傳》等專書之後,發憤編成《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自一九二〇年代起,迄於一九四九年止,計收七家二十五種作品,無一不是曾在武俠小說發展與演變過程中,具有代表意義、而深受讀者重視的傑構。這部「大系」一出,至少,後之學者若對這個時代的武俠文學盛到興趣,可以不再有「痛往籍之日衰,懼來者之無徵」的慨欺,而一般讀者若對這些早年曾經風行中國全境、引起熱烈迴響的作品感到好奇,也不致再有無緣得睹盧山真貌的遺憾。
葉洪生先生為了編成這部《大系》,使無遺珠之憾,曾經耗費無數心力,動員無數朋友。港臺各處的書肆畫坊、私人收藏,歐美、日本各地的大學圖書館、資料陳列館,乃至當年武俠名家的朋儕與後人(如還珠樓主的長子李觀承先生),均是他與友人不斷訪尋的對象。在堆積如山的冊籍中披沙瀝金,確定七家二十五種作品之後,又不憚煩劇,一一考訂版本,分段標點,整飭承接轉換之處,以便利現代讀者閱讀。然後,再賦予每種作品通篇的導讀與分段的批註,其用力之勤,用心之苦,實非常人所能想像。筆者忝為洪生兄的多年知交,深知洪生兄微意所在,是希望為中國近代民俗文學的這一支流裔,留下真實的軌跡與紀錄,使這些有價值的民俗文學遺產,不致因時代的動盪與學界的漠視,而遭到沉冤莫白的命運。至於珍惜民俗遺產,其實亦正所以珍惜民族文化,自不待言。
值得深思的問題
而無論人們如何看待武俠小說,它在讀者羣中長期受到歡迎與喜愛,是一項不容否認的事實。也許,若干年後,人們將會發現,在分工日細、節奏日快的現代社會裏,中國文化中有許多根深蒂固的理念,竟是藉著武俠小說而普及與流佈下去的,甚至,許多中國歷史的故事、中國地理的景觀、中國民間的風俗、乃至中文寫作的技巧,也透過武俠小說而極自然地印入到大眾的心中。
由於葉批《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的出版,早期武俠小說的精華,已具體呈現在大家面前。將武俠小說正式定位為中國民俗文學中值得重視的一個切面,似乎已經是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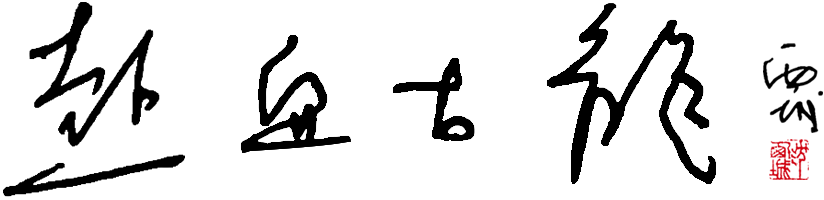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