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师承考》(刘国重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6月
后记改革开放之后不数年,“武侠热”即在大陆地区兴起。那年月,不读武侠小说的读书人,并不很多。
何以一“热”至于此?
那年月,没得选,可读的书仍太少。那年月,初“解冻”,种种禁锢仍待解放。天马行空、不守法度的武侠小说,于是大受欢迎。
那么多人、那么多家庭,此前十数年,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武侠小说,遂风行一时。
我的中学生涯,五六年间,课上课下,都在这“武侠热”中,昏昏度过了。当然,武侠小说之外,也还读一点各类杂书。
饥不择食。只要是武侠小说,拿起来就看。好作品读了不少,劣作更多。
不少同龄人,提起当年的阅读经历,有恨恨之意,似乎自己未能成长为“超天才”,都怨武侠小说及其作者。
此意,我没有。
即便少年时我没读过那么多武侠小说劣作,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自己什么材料,也还知道。没人逼我,是我自己的选择。至少多识几个字,知道多一点事。不应有恨。
无论是“武侠小说”(或“通俗文学”),还是“纯文学”,总是劣作居多,佳作绝少。
李劼先生从来不把金庸小说看作武侠小说,“正如我不会把《红楼梦》看作是言情小说一样”。李先生此言,可与陈世骧先生谈《天龙八部》时所说“艺术天才,在不断克服文类与材料之困难”对照看。
《红楼梦》所写,仍是才子佳人,但是极大地突破了“才子佳人小说”这一“文类”的限制(“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这话,是小说中贾母史太君说的,也代表了作者本人的意见),就不(仅)是“言情小说”。
金庸小说,尤其后期几部小说,也突破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限制,就不(仅)是“武侠小说”了。
刀尔登先生长我数岁,也一直是金庸小说的热心读者,以为不管什么时候,抓起一本金庸小说就看得下去。然而,约2014年,重读某一部(似为金庸早期作品《射雕英雄传》),发现读不下去。刀先生由此感觉可能是自己“长出息了”,第二年写出一篇《通俗小说》,谈对金庸小说的新看法。
刀尔登先生将小说分为“文学小说”“通俗小说”两种。二者的分别有二:是否“情节推动”;是否“总想着取悦读者”。
刀尔登先生说,读“文学小说”,总觉得“磕磕绊绊”,经常纳闷:“这是什么意思?老天爷,他写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鄙人则认为,这种小说,照样有“取悦读者”的嫌疑。
读者和读者,是不一样的。有些读者,所喜悦的,正在这“磕磕绊绊”。
作者和作者,是不一样的。同样写“磕磕绊绊”的小说,有的作者几乎不考虑读者的喜好,某些作者却完全可能投某些读者之所好。
所写小说,不够“磕磕绊绊”,或可获得更大商业利益;写“磕磕绊绊”的小说,却也可以猎获很高的社会地位;我不敢断定,对于所有小说家来说,商业利益必然更诱惑。所谓的“文学小说”,
就像所谓的“通俗小说”一样,不能免于“取悦读者”的嫌疑。
直说作品的好坏就可以了,很具体地去断定某一位小说家的“动机”如何,并且“总”是有着这样的“动机”。这一套,不仅无聊,并且全然忘了自己还是“人”,并不“全知全能”。
“总想”取悦读者,一定写不出有价值的作品。这一点,我与刀先生同一意见。但我感觉,稍微写得好一点的“通俗小说”,其作者都不可能“总”是想着取悦读者。一意求荣,往往得辱极深。即便是“通俗小说”的读者,也不是那么容易哄骗的。
无论写的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只要并不“总想”,只在一二方面试图“取悦读者”,可以写得稍好,也可能写到极好。梁实秋先生认为,莎剧中那么多的色情元素,很可能就是莎士比亚试图取悦观众。梁先生闲闲说来,并不认定这就是“坏事”,更不因此而否定莎剧的价值,这样猜测莎翁的“动机”,就没有问题。不可随意把人往“坏”处想,是基本教养。
金庸似乎并不自觉“总想着取悦读者”,否则,他在《笑傲江湖•后记》所言“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就是弥天大谎。通过武侠小说认识“政治生活”,多数武侠小说读者有这样的爱好?不好如此断言吧。
金庸后期几部作品,包括不很长的两部长篇小说《连城诀》与《侠客行》,写得尤其好。但这两部小说,在读者中,至今不很受欢迎。这样的结果,金庸写这样“另类”的武侠小说时,完全预料不到?不好如此断言吧。
约1980年,金庸在一次访谈中说,希望自己的小说“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温瑞安等《金庸茶馆》第三册)。明明“总想着取悦读者”,却说出这种话,给自己脸上贴金。如此金庸,有些“厚颜无耻”了。
刀尔登先生又指出,“通俗小说”与“文学小说”的区别,在于“情节推动”与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在欧洲,现代小说的形式确立之前,几乎所有小说,包括最伟大的一批作品,都是以情节为最主要推动力的。”这就奇怪了,既然“情节推动”曾经写出过“最伟大”的小说,何以现时代每一部“情节推动”的小说,就永远“通俗”,该遭鄙视呢?
刀先生辩说:“近代小说中的那些经典作品,之所以逃过了‘通俗小说’或‘类型小说’的恶名,只因为作者是啰唆鬼,不是简简单单地讲出一个曲折的故事,而记下了对社会、对人生的大量观察。”这话,与前面所引金庸1980年那几句夫子自道,怎么就那么相似呢?金庸也不以简简单单地讲出一个曲折的故事为满足,至少他本人是这样说的。我们不好随随便便就判定他人在撒大谎吧。
1969年,在金庸的书房中,王敬羲先生谈及一部“近代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他说:“譬如《汤姆•琼斯》,最初的写作目的还不是为了娱乐?现在我们谁也不能否定它的文学价值。”林以亮(宋琪)先生帮他补充,说:“菲尔丁最初写这部小说,他的出发点已经不单纯为了娱乐读者……这才会出类拔萃,成为后世传诵的文学作品。”以金庸的个性,自然不会顺势攀附菲尔丁,只有当王敬羲先生逼问:“金庸先生,你在你的作品里,有没有一边娱乐读者,一边也尝试放进一些自己的道德感、人生观,以及对这个时代的批判呢?”金庸这才含蓄而谦抑地表示:“近来也有在这方面尝试的企图。”(温瑞安等《金庸茶馆》第三册)
《汤姆•琼斯》等“近代小说中的经典作品”,有“娱乐”(“取悦”)读者之嫌疑,“是以情节为最主要推动力的”,并且,读起来居然并不“磕磕绊绊”!即便在刀尔登先生看来,它们也都是“最伟大”的,竟“逃过了‘通俗小说’或‘类型小说’的恶名”。同样具有这三特点的金庸小说,未必就有很高价值,但也未必就没有很高价值吧?不能断言它们永远逃不过“通俗”之名吧?如此断言,不说别的,至少逻辑上讲不通的。
读来并不如何“磕磕绊绊”的“近代小说”中,只有少数好作品;读来“磕磕绊绊”的“现代小说”中,好作品仍只占少数。“磕磕绊绊”与否,就没有资格成为衡量小说好坏的标准——至少,逻辑上是这样的。
谈金庸,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只希望能做到诚实,不敢妄想自己有多么正确(没有人可以代表真理)。我对金庸小说评价很高,十年来,诚实地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成文数百篇,涉及金庸和他小说的方方面面。哪一天,我要是像刀先生一样,也“长出息了”,看不上金庸小说了,希望那时的自己,能同等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我所能做的,只是一一直言金庸小说的种种不足,绝不会先给贴上“通俗”或“市场”的标签,以为否定了这一标签,就一举否定了金庸小说。
在刀尔登先生看来,《水浒传》一书,虽则有着丰富的“文学性”,仍属“通俗小说”,达不到他眼中“文学小说”的标准。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现当代成千论万的长篇的“文学小说”中,有哪一部,写到了《水浒传》这部“通俗小说”的高度?
文体(或文类)无高下,成就有高低。小说,只分两种,好小说和坏小说。其他,像刀尔登先生这样以“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分别,或者像易中天先生那样以“非市场文学”与“市场文学”的分别,来判定优劣,都是不合理的。
没有人可以代表真理。我对金庸小说评价很高,而刀尔登先生看低金庸小说的价值。彼此结论不同,我不敢说正确的必定是我。我所敢说的,只是刀先生这种“贴标签”的论证方式,完全没道理,根本站不住。
惭愧,迄今未能“长出息”,金庸小说,尤其他后期几部作品,一直还能读下去。当然,期间也读过一点其他的杂书。其中很有些是金庸也读过的。读来往往有似曾相识之感,有所会心,觉得金庸小说或由此得到启发。
毋庸讳言,金庸小说“挪借”自前人作品的情节,为数偏多。窃以为,这丝毫不影响《金庸作品集》的价值,作者金庸的文学成就,或可因此稍微打个折扣。
此书论列的可能影响金庸创作的文学家,除了梅里美与王尔德,其他,包括莎士比亚、曹雪芹在内,都是“通俗”的,至少是曾经“通俗”的。只是,很多读者早已忘记他们的低俗出身。
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字,四年来,曾陆续发表在胡文辉先生编辑的《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中。有几条资料,还是胡先生想到,为我补足的。我写文,向来很不“学术”,当时未曾注明,这里一并致谢。
胡先生认为:“海内外在世的中国文化人物,登峰造极者有三人:金庸,余英时,罗大佑。”每一字,都是我所赞成的。当然,此论不会因为我的赞成而更正确。正确与否,未来的世纪,会给出答案。
2016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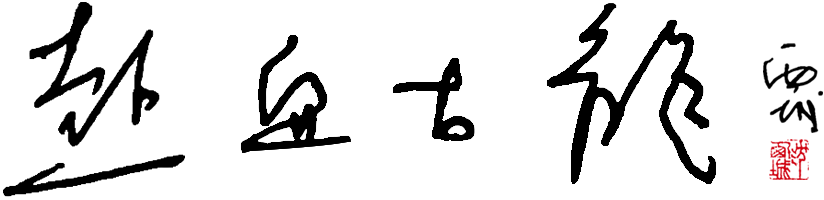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