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通俗文学十五讲》,范伯群、孔庆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武林盟主
如果说,中国通俗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作家是张恨水的话,那么20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作家,则非金庸莫属。
金庸从50年代成名开始,他的创作长盛不衰。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金庸作品进入了各种文学史、进入了大学课堂。严家炎先生从四个方面来论述“金庸热”已经成为“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覆盖地域广,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1]不过张恨水与金庸的区别之一是,张恨水以社会言情小说为主,而金庸则是专门的武侠小说大师。50年代之后,新派武侠小说在港台等地崛起,涌现出许多著名作家,而大多数读者和研究者公认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的当世第一人。
中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从唐宋传奇到元明小说,历代都有佳作。清朝后期,武侠小说陷入衰落,武侠人物沦为朝廷的鹰犬。至1923年,现代武侠小说兴起,产生了“南向北赵”和后来的北派五大家等武侠名家,是为“旧派武侠小说”。50年代,梁羽生、金庸先后出道,新派武侠浪潮从香港发端,迅速波及到中国的港、澳、台及新、马等广大亚太地区。至60年代,台湾武侠四大家古龙、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等群雄割据,把台湾武侠推向高峰。一时之间,名手如云,加入武侠创作队伍的大约有400人左右,作品上万种。就在这汪洋恣肆的武侠大海中,金庸技压群雄,始终保持独执牛耳的“带头大哥”地位,以炉火纯青的造诣,登上了“武林盟主”的宝座。
金庸在群雄逐鹿的武侠创作队伍中,作品并不算多。他从1955年“下海”,至1972年封笔,连长带短,一共只有15部作品。但是这15部作品,每一部都出手不凡,每一部都别开生面,每一部都名震江湖,给人留下过目难忘的深刻印象。他吸收了旧派武侠成功的艺术经验,把“纸上武学”发扬光大,塑造了数以百计的栩栩如生的武林人物形象,发明了许多神奇绝妙的“纸上武功”,使武侠小说进入千家万户的普通生活,为武侠小说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荣耀,以至于金庸成了武侠小说的金字招牌,假冒金庸、模仿金庸的作品成百上千。金庸以他震古烁今的卓越“武功”,成为中国武侠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武侠革命
严家炎先生指出:
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2]
金庸对武侠小说的革命,最核心之处在于对现代精神的自觉追求和深入开拓。以往的武侠小说大多充满血腥暴力,鼓吹盲目复仇,而金庸的小说反对冤冤相报,主张神武不杀。以前的武侠小说充满封建观念和陈腐伦理说教,而金庸的小说高度张扬人物个性,充满民主自由的现代观念。以前的武侠小说模式僵化,武功荒诞,而金庸的小说推陈出新,力避雷同,武功既神奇,又不失现实生活依据。坚持写人性,坚持人民性,坚持社会批判性,是金庸小说始终不渝的倾向。这在梁羽生、古龙等其他新派武侠小说家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他们和金庸一起超越了旧派武侠,建立了气象万千的新派武侠世界。
而金庸不仅超越了旧派武侠,他甚至突破了武侠小说的园囿,为整个通俗小说带来革命性的启迪。金庸以小说为载体,全面弘扬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金庸小说中,渗透着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滋养,而又独铸伟词,自成一家。金庸的小说语言,高雅大方,传神洗练,既克服了“新文艺腔”,又充满现代魅力,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开辟了一个辉光、博大的境界。金庸不但使所有人对武侠小说刮目相看,也使创作武侠小说不再是一种被人轻视的雕虫小技。金庸不但光复了由唐传奇和《水浒传》等优秀作品所建立的中国武侠小说的赫赫声威,而且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能够在现代化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与任何一种小说形式抗衡望宇。
金庸对武侠小说的革命,并没有使他的小说不再是武侠小说,他在提高武侠小说艺术境界和文化层次的同时,仍然极力保持着小说的通俗性和娱乐性,不像许多所谓纯文学作家那样,为了表现自己的思想深刻,而使小说生涩枯燥,像个瘪三。金庸不一味求雅,而自然高雅;不一味避俗,而永远通俗。这是一种不走极端的成熟干练的真正“革命家”的气度。金庸对武侠小说的革命,“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3],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小说巨匠
金庸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是“武林盟主”和武侠小说的革新大师,跳出武侠小说的范围,放到整个文学世界里来看,金庸也不愧是一流的小说巨人。
金庸的武侠作品,从小说艺术的方方面面来衡量,都是精湛的、上乘的。从结构上看,金庸做小说,如同一个高明的建筑师,“一篇有一篇新形式”[4],一部有一部新妙思,每部之间“远近高低各不同”,一部之内,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大有大的宏伟,小有小的玲珑。既有现代小说的严密、系统,又有传统小说的疏朗、自然。
从人物上看,金庸小说所塑造的深入人心的典型人物,其数量之多,可称是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通读过金庸小说的读者,随口即可说出几十个活脱脱的人物,如在目前。金庸笔下的人物,既有性格丰满、层次复杂的“圆形人物”,也有性格单一、褊狭古怪的“扁形人物”。他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来自于深厚的生活土壤,另一方面又符合社会学、心理学的深入分析。金庸塑造的这些艺术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
从情节上看,金庸小说一方面吸取了侦探小说的特长,悬念迭生,惊险紧张,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中国传统小说固有的闪展腾挪、起承转合的章法,张弛结合,有徐有疾。金庸小说还大量化用现代的电影戏剧技巧,大小场面搭配得当,多条线索详略分明。欣赏金庸小说的情节,如同在做一套优美的心灵体操,能够得到极大的精神享受。
从语言上看,金庸的人物语言,必定是合乎人物的性格、命运、处境、心态,“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5];金庸的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金庸“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6]。金庸在雅语与俗语,景语与情语,白话与文言,官话与方言等诸多语言关系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创造出一种英华内敛,渊停岳峙的博大精深的小说语言。论者概括金庸小说语言的境界为:“语到极致是平常。”[7]
在这些具体小说手法之上,金庸小说“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8]。金庸写武侠而超越武侠,他的武侠已经成了各种人生活动的极好象征。读者可以从中领受到学习、工作、交往及人生修养等许多方面的感悟,从中体味人性的丰富哲理和妙境,这是大部分“纯文学”小说家也望尘莫及的。曾有学者排列20世纪中国小说家座次,金庸位居第四,又有多家报刊调查20世纪最受欢迎作家,金庸皆位列第二,仅居鲁迅之后。金庸的绝世才华和卓异创造,昭示出了一位当之无愧的小说巨匠的艺术风范。
注释:
[1]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第8—13页。
[2] 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3] 金庸:《天龙八部》附录之《陈世骧先生书函》。
[4] 茅盾:《读〈呐喊〉》,原载1923年10月8日《文学周报》。
[5]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
[6] 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第152页。
[7] 见孔庆东、王伟华编:《金庸侠语》序。
[8] 王国维:《人间词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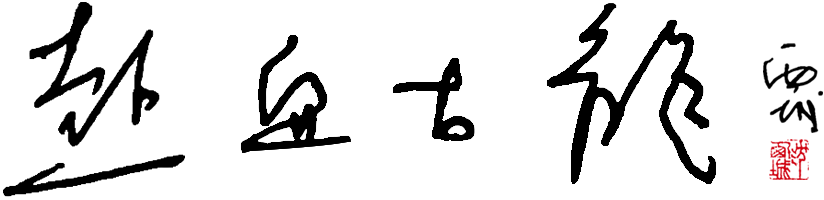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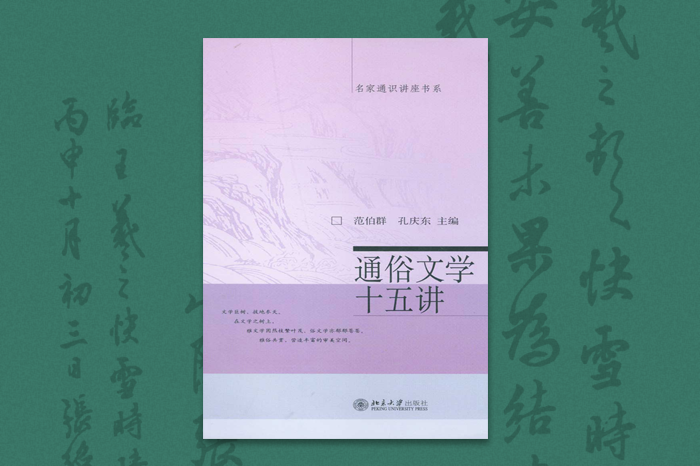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