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爱敢恨求死得死古龙很爱朋友,常召朋友来喝酒尽欢,朋友醉倒在他家里,正好可以使他免去筵散的凄凉。
一九八五年,古龙逝世的那个深夜里,记者问我的感觉,我说:“顿失所寄。”
也许是我语意含糊,或许编采人员认为此句无关宏旨,所以,在次日香港“明报”世界新闻头版刊出金庸、倪匡和我对古龙粹然去世的看法时,访谈内容完整无缺,但并没有记录这一句话。
但这是实话。由衷的话。
我认为这世上没有人比我对古龙“爱”得更深。
我在念初中二的时候,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一个小山城:美罗阜,有幸且偶然在那小阜里唯一一家“半正规”的“联友”书局里,买到一册一个骑着白马走过一片绿柳红袍侠客为封面的:“多情剑客无情剑”之下半册。从此,我就迷上了古龙。
不错,当时现代文学予我极大的吸引力,但不似古龙作品来得更致命。现代文学那种自怜、自负、自卑、自大而有自命不凡、自掘疮疤、自以为是、自寻烦恼的特色。
但,古龙作品里都有,但却写得平易近人,深入人心,而且更没有故弄玄虚、固步自封。在这之前,在这之后,我读过无数、无算的武侠小说,但能使我不致待(呆)在纯文学里执迷不悟、饮鸠自尽,而又保持以文学的精粹跟广大读者群众同心相契的本色,古龙对我,确有育功。
我十六岁时在香港发表第一篇武侠小说:“追杀”,笔意格局,完全是因袭古龙的。我可以说自己十分钟情于金庸的小说,但古龙绝对才是我武侠小说创作的“启蒙老师”──当然他从来没在实际上传授我什么,但在他的小说里,有的是发掘不完的宝藏。
一九七七年,在台北,“联合报”的痖弦给了我一通电话,要我跟古龙出席一个武侠小说的座谈会。那是我第一次跟古龙会面。当时,我说了几句客气话,古龙马上就说:“太谦虚就是虚伪了。”
直至我在台北发生了“冤狱事件”之后,我听“万盛出版社”的负责人说,古龙特别向他要了全套我的书,而且看完。一九八七年,我回到台北,听到古龙的至交们提起,古龙在生时说:“温瑞安只要对武侠小说写得再集中一些,运气也再好上一些,那武侠小说以后就看他的了。”
古龙是浪子,浪子比较自由浪漫,也比较易受人误解和鄙夷。他不像金庸。金庸是人称“大侠”,而且也是巩固的屹立于现实人间的“大豪”,举足轻重。
坦白说,在个性上,我甚爱古龙,因为他甚可爱。甚至可以说,连同在作品上,古龙也甚可恨,我常恨他的小说“落雨收柴”、“雷大雨小”或“千篇一律”。
总之,古龙的可爱和可恨,乃因他就是性情中人,就连他的故事和文学,也一样大情大性,一点也不虚伪。爱他是因为他能超越别人,恨他是因为他难以超越,而他自己也一样超越不过他自己所建立出来的规范,这点对真正懂得欣赏和发掘古龙的长处和缺点的我而言,无疑也是可恨的。
他敢爱敢恨,求“死”得死。他再次因肝硬化而送医院急救时,医生力劝他戒酒,他的笑声响彻整座医院。他爱朋友,常召朋友来喝酒尽欢,朋友醉倒在他家里,正好可以使他免去筵散的凄凉。他怕寂寞,他重感情。常对着一栋空白的墙说话。这些都跟我性情一样。我办“绿州文社”、“天狼星书社”到“神州社”、“朋友工作室”、“自成一派合作社”,都是一种笑拥寂寞,紧握刀锋的悲歌手势而已。
没有人可以象我那么“爱”(或曰“恨”也无妨,反而古龙这种人绝不会介意。)古龙,因为迄今仍很少人、太少人,几乎没有人像我一般在他生前死后对现在武侠花了那么多心血和心机。如果有人办古龙特辑(另一位是政论家哈公)而没有请我写专文(就算没有稿费可拿)纪念他,我都一定会“同他有仇”,因为我是古龙专家、古龙忠实读者、古龙精神的接班人(至少在武侠小说上),所以,他死了,我一度:“顿失所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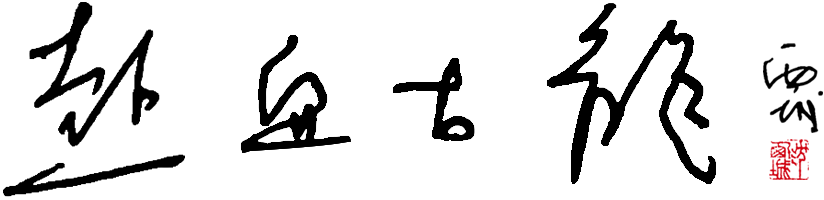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