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正文
读古龙小说读得多了,我在偶然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古龙笔下的英雄人物(或者说正面形象)的兵器,用刀的居多。楚留香与陆小凤自然是不用兵器的,李寻欢与叶开用的是“飞刀”,萧十一郎用的是割鹿刀,傅红雪、丁宁、姜断弦、花错、朱猛,用的都是刀。我并非认定古龙笔下的侠客不用剑,如西门吹雪与阿飞就是有名的剑客,但古龙在兵器中特别偏爱刀,这也是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当然有作者的深意。古龙在《关于飞刀》(《飞刀,又见飞刀》的序)一文中讲得很清楚:“刀不仅是一种武器,而且在俗传的十八般武器中排名第一。”他还把刀与剑作了比较,他认为:“剑是优雅的,是属于贵族的;刀却是普遍化的,平民化的”“剑有时候是一种华丽的装饰,有时候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某一种时候,剑甚至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刀不是”。
古龙这一段对于刀剑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自古以来,剑是登堂入室的,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贵族公子,都爱佩剑,连李白、陆游这样的大诗人也与剑结下不解之缘。吴均、杜甫、白居易、贾岛、韩偓、李群玉、王世贞均留下咏剑诗。这是因为剑本身具有一种高雅飘逸与浪漫神秘的气质,同样显示了它主人身份的尊贵。古龙又这样认为:“有关剑的联想,往往是在宫廷里,在深山里,在白云间。”而刀呢?它似乎比剑普遍寻常得多,它虽然是猛士的兵器,但更多使用它的是无名小卒,其身份与帝王、将相、公子、儒士,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刀却是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古龙语)。因为,人出世以后,从剪断他的脐带的剪刀开始,就和刀脱离不了关系,切莱、裁衣、理发、修须乃至示警、扬威、正法,哪一样离得开刀呢?在人类的生活中,刀简直与水与阳光一样重要。可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刀远比剑普通和不引人注目。而在某种意义上,刀又比剑更野蛮、更残酷、更凶悍。总而言之,刀的名声与剑相差甚远。古龙这个奇怪的发现,使我想到了一个作家的思想意识。古龙如此推崇刀,因为他的创作意识是属于平民的,他的作品也是属于大众读者的。
我们不妨以他的作品再作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与《三侠五义》,都是把侠客歌颂为执法的对象,也就是官府的帮手。他们一方面除恶惩奸,另一方面又效忠于皇帝。展昭如此,黄天霸更是如此。从这一点上,《水浒》的基本思想也是“只反官府,不反皇帝”“只反贪官,不反清官”。再以新派武侠小说而言,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也因袭了这种传统忠君意识,古龙之后的温瑞安则写了《四大名捕》来歌颂为官府除恶的冷血、追命、铁手、无情四个捕快。可以这样说,他们的立足点是站在人民与清官的共同立场上。而古龙小说的侠客却不同(当然他在《血鹦鹉》中也歌颂过捕快,但这只是绝少见的艺术形象),他写李寻欢、楚留香、陆小凤、江鱼儿、叶开,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都敢于与官府、甚至与传统的统治思想作彻底的对抗。如陆小凤与官府爪牙金九龄斗智斗勇,就写得十分生动;又如西门吹雪的深入皇宫。他们身上,体现了古代侠客蔑视君权与官府的凛然正气。古龙这样塑造人物形象,正在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使自己笔下英雄的气质更接近于普通百姓,并让侠客之根深深地扎在老百姓之中。我以为,这是古龙作品的进步意义之一。
同样从作品艺术风格来看,古龙也显示了他的平民创作思想。他在《新与变》(《大人物》序)中强调这一点:“写小说,当然是给别人看的,看的人越多越好”。可见,古龙要求自己的作品应该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他有感于有人看不懂武侠小说,决心求新求变。所谓“变”,也就是把文字写得更简单明了,把对话写得更加生活化些,使作品更加有人情味,于是他提出:“我们若要争取更多的读者,就要想法子要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想法子要他们对武侠小说的观念改变。”古龙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不仅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传统武侠小说的情节性,而且吸收了许多西方思想与欧美创作方法,他努力把各种文学精华融会贯通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新的民族风格的文学--当然这是一种更加大众化的文学。
从古龙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来看,他确实很注意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在评论家与读者的见解有分歧时,他总是倾向于读者的青睐。他小说的文体也力求去除生涩干枯的毛病,同时让古代侠客的思想、情感与现代人有所沟通,并注意对话的生动性与口语化,这都与他为广大读者创作的旨意相吻合。
古龙的许多小说已搬上了银幕(他自述有两百多部武侠电影--见《风铃中的刀声》序),经过电影的传播,他笔下的形象更大众化了。他曾经这么说:“从某一种角度看,大众化就是俗,就是远离文学与艺术。可是我总认为在现在这么一个社会形态中,大众化一点没有什么不好,那至少比一个人躲在象牙塔里独自哭泣的好(见《飞刀,又见飞刀•序》)”。这难道不是一种平民思想的典型反映吗?
今天,古龙小说能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除了其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之外,恐怕也与古龙的创作思想--平民意识--有着必然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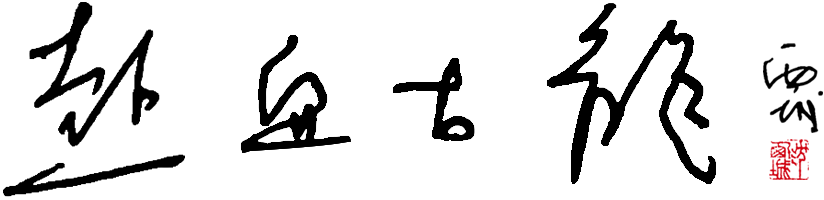

评论 (0)